
2021年的春节,一二线城市因“就地过年”而变得前所未有地热闹,本地生活服务业也随之迎来一波“反弹式”增长。
那些在北上广深送外卖、干家政、做推拿的从业者,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县城乡镇的小镇青年、农村青年,他们在城里过了一个“全勤营业”的春节。中国劳动学会和国务院参事室的调研显示,今年有77.61%的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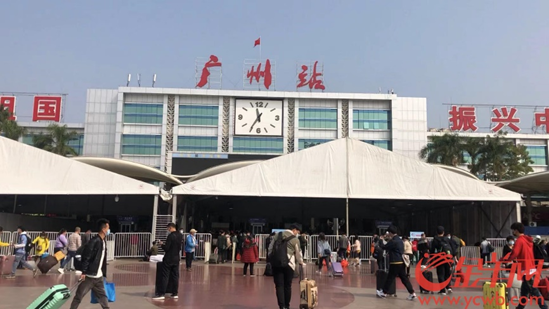
但他们的县城、小镇,并没有因为他们不回家而变得冷清。
因为小镇上不乏年轻的面孔。
而且,许多人显然不是那种风尘仆仆从大城市回到家乡的打工人,有人拥有自己的小汽车,有人在为刚买的新房挑软装,许多女性热衷聊的话题是怎么把小朋友送进县里最好的幼儿园。
在2021年春节前夕,瞭望智库联合蚂蚁研究院,共同发起了一个返乡调研。过去一个月,我们分别走访了贵州、陕西、山西、安徽、河南等几个省的县城,访谈了数十位回家就业或创业的小镇青年。
我们发现一个隐然成型的新趋势:中国小镇正在重新热闹起来。这个新趋势还有待权威的基本面数据支撑,但在此之前,仍然值得我们抛出来,供大家一起关注和探讨。
1
家门口的新机会
不可否认,这些回家的小镇青年,相当一部分比例是出于居大城市不易的无奈:生活成本过高,入不敷出;在大城市的小生意维系艰难;一些女性则是因为要生育或照顾孩子。我们调研的对象中,很多人回乡之前,并没有明确的下一步规划。因为中国县城和小镇缺少适合以及能吸引到年轻人的工作机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但当他们回到家乡,发现了一些之前所不知道的机会。他们可以进入家附近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也可以从事像云客服、人工智能训练师这样的数字新职业。
这些新机会,都是随着产业和互联网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下沉市场涌现的。这些新机会在就业容量上还远没法和大城市相比,小镇青年们的优先选项仍然是先到大城市去闯一闯,但是它们确实给小镇青年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在家门口就能把小日子过好,背井离乡到大城市去不再是近乎唯一的选项。
因为这次联合了蚂蚁研究院,我们这篇回乡观察就聚焦在家门口的数字化就业。
这些数字化新就业机会一是随着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而来,基于成本的考虑,它们大量转移到了下沉市场,或转移到了线上兼职平台。二是随着互联网下沉,将城里人的数字化生活方式拷贝到县镇,从而在当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外卖小哥、跑腿、社区团购运营等。
这些新工作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能提供的收入低于大城市的打工人,但在县城里却富于竞争力。
除了收入红利,小镇新青年们还手握一个政策红利: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政策红利能让他们近乎零门槛地在县城落户,这意味着这些县城新中产、新精英们能在县城买房、买车、孩子能上不错的学校,从而拉动了县城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当地消费以及消费升级,进而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公开数据也能印证这一趋势:近几年在县城购买住房的人口从原来的1%上升到了20%。
这改变了小镇青年此前的奋斗路径:中学或大专毕业就外出到附近的大城市打工,极少消费,大部分积蓄都寄回家乡盖楼、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消费、以及家庭生活是完全分开的。但回到家乡,曾经被分割的人生重新整合在了一起。

2
兴起的云服务小镇
毛蜜蜜是从北上广深“撤退”的其中一位小镇青年。
从下决心离开北京之日始,包括之后的两年,他做了很多传统打工人难以理解的选择。
第一,放弃了扎根北京的机会;
第二,放弃了时髦的互联网职业;
第三,在最不具投资属性的西部县城买了一套123平方米的房子。
毛蜜蜜用自己的选择证实时代变了。曾经只有大城市可以安放的青春,如今即使回到小镇也不算难。
“了解网络、有电脑”这种在北京属于就业地板的条件,却让他在老家,山西临汾市洪洞县靠给支付宝做云客服,一个月有七八千块,最高时有一万多的收入,这一收入远高于当地的平均薪资。
26岁前就买了房,在洪洞县,毛蜜蜜实现了。
当中国一只脚踏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要抬起另一只脚的挑战——
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
传统制造业发展到极限,产业升级却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高收入工作的占比总是那么小;
广大后富地区如何才能不被先富地区拉开更大的差距;
……
毛蜜蜜们的选择让我们看到抬起另一脚的新的可能性:让更多生活在农村,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也能从容生活。
蚂蚁研究院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蚂蚁云客服平台迄今共有3.8万兼职者。他们主要生活在中部县城,女性居多,占了72%;他们都很年轻,平均年龄28岁;兼职状态比较稳定,最长的一做就是七年。
小镇青年在家门口为大型互联网公司、电信运营商做客服的机会越来越多。微信、京东、拼多多、电信、联通、移动……都分别将人工客服大量外包出去。
仅阿里巴巴迄今就已累计培训人数38万人,超过13万人成为其在线客服。
另一种情况是建云服务中心。出于成本和助力脱贫的考虑,互联网平台的云客服基地基本都设在中西部县市,以及曾经的那些国家级贫困县。
黑龙江泰来县、七台河市,河南新乡……已经开始对外主打“云服务小镇”的名片。这些缺乏资源和产业支撑的城镇,因为互联网的下沉,开始出现人口回流。
泰安2018年数据显示,在小镇上做云客服的年轻人达1160人,占全县新增就业人数的一半以上。


3
在大山里给人工智能打工
“云客服”这种职业,一度让毛蜜蜜的邻居亲戚很不理解——天天呆在家看电脑,也算是正经工作?
在缺乏包容度的小县城,毛蜜蜜的父母为了躲避闲言碎语和好奇的打听,甚至减少了出门。
其实,数字技术一直在催生“让人看不懂”的工作。如今,它的影响下沉到了洪洞这样的小县城。
要保证中国人人均收入有较快增长,服务业是其中一个关键。原因一是服务业可以吸纳较多的人就业,二是其薪酬整体高于农业和初级制造业。
但许多人对服务业往往有偏见,以为是干干餐饮、端端盘子。
事实上,服务业升级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方向:
其一是质的升级,这主要是指金融行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这一块是北上广深这个量级的城市需要突破的方向。
其二是面的普及,这主要是指技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下沉,是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有超出想象的巨大空间,并且已经在中国城镇创造出了众多的数字新职业,为共同富裕提供了一条路径。
比如“人工智能培训师”,这个职业几乎就是为小镇青年量身定做。它被收入了人社部的新职业目录中,是训练人工智能不可取代的一环。
陕西清涧人杨彦军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他日常的工作是给书的标题、目录、正文进行标注,平均两天能标注完一本书。
在当下,人工智能需要在这些标注的帮助下学习并变得聪明。
杨彦军在深圳打过工,在台州开过蛋糕店,回老家是被动的选择,蛋糕店生意一直不太好。刚回到清涧时,杨彦军能找到的工作就是在工地上搬水泥。最终是接到当地扶贫办的电话,推荐他应聘一家当地公司,成为一名人工智能培训师。
这家公司的合作方是当地扶贫办,以及支付宝。2019年开始,支付宝公益基金会将其数据标注的外包工作定向落地到贵州、陕西等国家级贫困县。目前已吸引到近千名年轻人回到家门口工作。
作为公司最勤奋的人,杨彦军最多每个月可以赚到1万块,他的同事平均月收入则是4000元左右,在清涧,这算高收入了。

杨彦军每天都是公司最后一个走的人。
更为关键的是这还是一份坐办公室,有社保、医保的工作。杨彦军对现状很满意,他希望未来可以去做一名专门培训新手的培训师。他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会需要更多的人来做这份工。
每天下班回到家,杨彦军都会给女儿讲晚安故事。
事实上,下沉的还不止这些数字新职业,还有互联网时代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从2017年开始,互联网平台不约而同开启了下沉运动,下沉到中国小镇、农村去要新流量,新市场。城里人能享受到的服务,眼下也纷纷复制到了县城、城镇:扫码支付、外卖点餐、共享单车、社区团购……
伴随新服务、新流量下沉的还有工作岗位,最典型的就是骑手,还有收钱码地推。在移动支付向下沉市场线下渗透的2018、2019年,仅是支付宝二维码地推,就有约170万人。
4
乡村飞行员
十多年前,社会上曾经流行着一句话——回不去的家乡。
这个家乡包括农村,也包括五六七八九线的城镇。所以,第一批逃离北上广的,过了没多久大多又回去了。
但现在,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新的分化,一方面,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减,另一方面,回老家成了越来越多小镇青年的选择。
2019年,中国进城农民工首次出现下降,而且一降就是204万,如果把在本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数量减去,就会发现越来越多农民工在老家就近就业。
比如中国外流人口最多的重庆,外流人口正在逐年下降;被誉为“中国吉普赛”的安徽,自2013年起已经连续7年实现人口持续回流。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张兵曾对外表示,人口单一涌向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历史已经改变。县城、乡镇将会重获发展良机。
小镇新青年们都会算一笔账:家门口的新工作,平均月收入普遍高于当地平均工资,刨去生活成本,能攒下来的钱也普遍高于在大城市打工能攒下来的钱。
除了各种数字新职业,像农民这样的传统职业也开始和数字化产生交集。
一部分农民随着电商的发展和下沉,成为兼职甚至全职的小店店主。淘宝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1年内,中西部淘宝镇、淘宝村增势迅猛,其中淘宝村数量同比274%。
300万淘宝村、淘宝镇,能够带动的就业超过800万,如果再加上拼多多、微商……可能已经有几千万农民摇身一变成为了电商从业者。
此外,和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开始在农村出现。
美国农业之所以发达,不是那300万农民,而是超过200万为农业生产提供直接服务的人。随着许多高学历的人返回城镇、乡村,中国最难啃的产业升级骨头也出现了突破的可能。
“乡村飞行员”是刘俊的头衔。他的工作就是通过手机接到订单,然后带上上无人机前往指定的农田,调好无人机的参数,无人机就会自己飞到农田上空开始喷洒农药,在操作的过程中,刘俊甚至可以玩会儿手机。作业完毕,刘俊把喷洒结果通过手机发给用户,用户确认后,完工。
可能从来都没有人能想到,中国农业也可以如此“性感”。
极飞科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近4万小镇青年回到家乡,做起乡村飞行员和飞行员培训师。

还有更“性感”的。通过手机和卫星贷款,江西农民刘迎峰承包的土地从几百亩扩大至上千亩。
这一新服务的原理是,用户通过手机上的LBS定位画出自家承包土地的范围,卫星向网商银行回传土地面积、作物类型、作物成熟度等信息,网商银行以此作为数字抵押物决定放贷额度。贷款还可以随借随还,适合像农业这样的周期性资金周转需求。
2021年过,刘迎锋打算再追加1000亩土地承包,顺利的话,年收入可达80万。这和他们小两口之前在外打工的收入相比,翻了七八倍。
四年前嘲笑和质疑她回家种地的亲友,纷纷前来投奔,从刘迎锋手中各自分包几百亩地,成了“二级分销商”。
第一次见到刘迎锋时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她长得太不农民了。刘迎锋皮肤管理得很好,和城里姑娘一样,她也喜欢出门化妆、买爆款裙子、穿高跟鞋、做指甲。他们一家四口平时住在县里,回村种地时,开的是凯迪拉克。
刘迎锋笑说,种地基本都机械化和数字化了,大家对农民的刻板印象也该变变了。
5
当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出现了外卖小哥
当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西藏墨脱出现了外卖小哥,当山西洪洞县都有了“生产型服务业”,当越来越多小县城摇身变成了“云服务小镇”……
我们感受到,重新热闹起来的中国小镇背后有着一些值得注意的慢变量。
第一,在生活消费上,小镇青年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大额支出和日常消费从割裂到合一。
过去,他们在大城市打工,工资基本不用于在城市消费,而是寄回老家。现在,能够在县城、乡镇找到工作并收入不错的年轻人,往往回乡三四年后,就会在当地买车、买房,从此安定下来。
越来越多安定的、有消费能力而且见过世面的个体与家庭,将进一步拉动县城的消费升级,商业活力,以及服务业的就业空间。
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这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家门口的新工作机会,大量来自于数字化相关,约五分之一更是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比如外卖小哥、快递员、移动支付服务商、单车运营等,他们的工作加持了县城数字生活服务的渗透度和丰富性。这让县城里的生活方式与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安徽颍上县,我们认识了一位叫吴海涛的饿了么骑手。他刚从大城市回到老家做外卖小哥时,发现县里还有好些餐馆没有上线外卖平台,于是在送外面的空隙一家家上门推广外卖平台。如今,当地餐馆几乎全部都能支持扫码支付、扫码点餐和在线配送外卖。
第三,在公共服务上,中国城乡差距也开始缩小,这也有利于吸引年轻人回流。
在江西新余,我们发现,当地政府因为手机上的数字公共服务已经做得足够全面,叫停了一座造价两亿元的市民中心的建造。
在中国最后一个接入国家电网的西藏阿里地区,甚至在2020年入网前,当地居民就已经能在支付宝上缴电费了,当地的医院,也可以用微信挂号和支付了;在因为接壤印度,去一趟还要办边防证的西藏亚东县,当地喇嘛都会在手机上充话费和缴纳寺院的电费了……

这些极值地区的状况,可以看出数字化公共服务在整个中国下沉市场的渗透度和覆盖率。
我们认为,这些以人为核心的变化,正在让中国县城热闹起来,并有望持续性地热闹下去。
小镇新青年在家门口有好工作、好生活、好的生活服务,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就越来越不再是近乎唯一的人生选项。这对于分流大城市人口,避免拉美、南亚、非洲等地区曾纷纷陷入的“城市病”,助力中国的城镇化,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