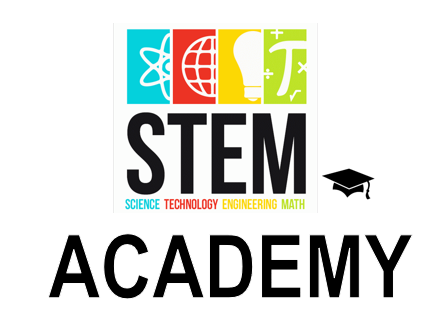李显龙总理:本区域国家比美国更尊重中国对疫情的处理方法
文 / 杨丹旭
4/10/2022

(早报讯)谈到冠病与抗疫工作,李显龙总理直言,本区域国家比美国更尊重中国处理疫情的做法。
李显龙总理不久前对美国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于当地时间4月1日到《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出席一场对话会。根据总理新闻秘书提供的文字记录,李总理就乌克兰问题、中美关系、新加坡面临的外来影响等问题阐述看法。
与会的《华尔街日报》编辑部人员提问,在美国看来,冠病来自中国,中国封城锁国不是最好的防疫方法,中国产的科兴疫苗也不是最有效。他询问李总理,本区域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处理疫情的做法。
李总理回应:“我认为太平洋区域比美国更尊重中国的做法。”

他指出,美国严厉指责中国一开始没有迅速发现、公布和消灭冠病,但实际上中国在一个月内就公诸于世,各国也争相作出反应。一些国家反应迅速,另一些国家如美国则后悔没有更快地作出反应。
李总理继续指出,美国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当初有可能处理不当以及处理方式不透明,尤其是质疑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漏。
他指出,当然中国人也许可以从一开始就更加透明,现在也可以更开诚布公地说明当初的状况。但当没有太多根据能证明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时,就要求中国证明病毒没有从实验室泄漏,中国人就会反问:我为何要开放我的实验室,以消除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和猜疑?
李总理也说,实验室里可能还有很多其他事物是中国不愿意透露的,这也合情合理。

【视频】李显龙总理出席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对话会(完整版)
4/02/2022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3月30日出席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会,活动由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主持。两人就乌克兰危机、国际安全架构和气候危机等多个议题进行讨论。以下是对话全文。
00:00 -【乌克兰局势的后续影响】
理查德·哈斯:首先,我想谈谈本周早些时候您与拜登总统会晤时发表的联合声明。我想特别引述声明的一句话:“乌克兰战争对印太地区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 我想请您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么说 又会如何影响?您能否具体地说明?
李显龙总理:乌克兰战争在多个层面都对亚太地区造成影响。首先,它破坏了国际关系框架中的法律和秩序以及国家之间的和平。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威胁到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尤其是小国。如果大家接受疯狂决定和历史错误为入侵他国的理由,我想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人都会感到很不安。

第二,事态的发展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损坏,已让全球多边合作体系,无论是在贸易、气候变化、预防大流行病还是防核扩散等方面,难以运行。我们之前能让敌对国家和竞争对手即便有分歧,也还是能以双赢的方式进行合作的框架 已不复存在。
当今格局是一个非赢即输的局面。你希望对方倒台,要修理它,并搞垮它的经济。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要如何尽可能地团结起来,相互合作,而不是陷入混乱、经济封闭或无政府状态?这对新加坡来说是一大隐忧,因为我们依赖全球化生活。
第三,乌克兰当前的危机必将对美中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这场危机必定会,也已经使关系紧张。我们希望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最高层级的联系能促成理性决策,而双方的关系也能保持下去。换句话说,我们希望美中关系不会变得比现在更糟,但这是无法预知的。尽管双方都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美中关系恶化,这将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个别国家也对乌克兰即将发生的事情作出具体反应。每个国家现在都会问,我们能从乌克兰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就国防而言,当我们需要帮助时,我们可以相信谁会向我们伸出援手,这样的意识在东北亚尤为明显。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已提出应该考虑在日本部署美国核武器。我相信一些参与战略课题的日本人此前已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安倍先生已将此课题摆到台面了。(日本)政府当然已拒绝这样的提议,并说他们永远不会这么做,但这个念头已经种下,而且不会消失,因为乌克兰局势显示了核威慑可以非常有用。
我想韩国也有同感。如果你看民调,大多数韩国人认为,韩国应该发展核能力,不仅仅是像以前一样部署美国的武器,而是发展它本身的核武能力。如果局势真的朝那方向发展,如果你是个乐观主义,你会说:现在朝鲜、韩国、日本、中国都拥有核武器,那我们已取得稳定的核平衡;如果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也拥有核武器,那将会带来更大的核平衡。你希望这仍是个稳定的平衡,但我认为我们正朝着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进。
至于谁会向你伸出援手,我想各国会做出一些考量。亚太区域的框架与欧洲的框架不同。欧洲有北约、有第五条款、有前华沙条约国家、有前苏联的共和国等。所以哪里是界限,哪里是不可触及的红线,情况都有所不同。在亚洲,我们并没有这些框架,但我们有台湾问题,有“一个中国”政策。而美国这一边有《台湾关系法》,但美中之间又有《三个联合公报》。我们应该如何诠释这些体系?局势又将如何发展?
以台湾目前的防务情况来看,他们希望能将兵役制度的服役期,从现行的四个月延长至12个月,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因为要让大家接受更长的服役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现在的民意是如此。还有另一项台湾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台湾出事他们认为谁会派兵帮忙,有40%的受访者相信日本会协防台湾,而30%的受访者则认为美国会派兵介入。在去年10月进行的类似民调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美军会出兵助台。
因此,我认为各政府会做出考量,他们不会一夜之间做出大转变,但这都是重要的战略性重估。我觉得除了要对乌克兰当前局势做出回应之外,我们也需要思考在亚太地区导向冲突的路径会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冲突发生。(一个国家)必须考虑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程序和联系,以及做出什么样的战略安排,以避免无法防止冲突而被迫进入防御状态。
在欧洲,学术界一直在针对乌克兰危机进行争辩。现实主义者如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如果北约没有东扩就不会发生今天的局面。另一些人则认为 ,乌克兰危机是无法避免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都已是北约成员。那在亚洲,我们没有北约,不过我们也有需要关注的热点,有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我们需要机制让处于对立的国家、对手与美国互动、中国互动、关系已密切的国家互动,让我们能够做出非常艰难的调整,那就是如何适应中国,一个更发达、体量更大、科技更先进,但同时不会对世界盛气凌人,并能被当今全球主要军事强国美国所接受的中国。
我们必须往这方面前进。我们有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它侧重讨论经济课题。我们也有东亚峰会,能让各成员国就战略性课题展开讨论,但在落实有关措施方面,该峰会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目前,美国有意建立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来联系本区域,不只以战略或安全和潜在敌意为基础,而是以取得双赢为基础。我认为你需要考虑到这一点,让事情能朝向一个不会导致激烈冲突的方向发展。
09:58 -【本区域对美国的看法】
哈斯:谢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意见和看法。在这个会议室里,我看到许多我的前同事。我们都曾参与联合声明的书写和签署工作。这份新加坡和美国签署的联合声明值得一读。它的实质内容比我所参与的许多联合声明都更充实。我不会代表你们当中的几位发表意见,但我确实推荐它,政府偶尔会信守承诺,而这是其中的一次。
您说了一些我想提出的问题,但我想跟进一下,那就是本区域对美国的看法。所以我的问题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为乌克兰提供了在我看来是“间接的支持”,包括在军事、外交和情报方面的显著支援。最明显的是经济制裁和其他措施,却并未提供直接军事支持。它拒绝了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也拒绝派兵参与地面作战,这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一点。这届美国政府在重要方面的做法和前任政府非常不同。
所以,当人们现在观察美国,美国在台湾和乌克兰做什么、不在做什么,这是否增强了人们对美国的信心?显然的,您不认为情况是如此。
李总理:我想各个情况都不同。正如我所说的,欧洲有北约,知道在北约课题上的边界在哪里。在亚洲 我们没有北约,我们有三个联合公报,在台湾问题上也采取了战略性模糊的政策。
我想大家都希望看到台湾能维持现状,即使有任何改变,也绝不能以武力或非和平方式发生。这是很难处理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经济或战略问题,而是关乎政治和民众情绪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哈斯:但您是否担心,由于俄罗斯可能会再次对欧洲秩序构成重大威胁,所以美国转向亚洲的战略不会实现?相反,美国在转向亚洲时,又几乎得绕道回去欧洲?
李总理:美国向来关注全球课题。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是乌克兰,就会是伊朗,或者是发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其他事情。你们不时也会关注拉丁美洲。所以我认为,我们接受美国在全球拥有广泛的利益,但亚太地区不仅有中国,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必须处理的。但另外,亚太地区也有许多美国的其他伙伴,当中一些是美国的盟友,其他则是你们的朋友。他们多数与美国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二战后近80年来,美国拓展了这些关系和利益,促进了这个全球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区域。因此,无论你有什么其他广泛的利益,这都是你无法舍弃的。我认为历任美国总统都明白这一点,并都亲自关注这个问题。但我无法想象他们因为只关注这个问题,而把其他的事情都排除在外。我也不认为他们会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忽略与中国的关系。我们所担心的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美国是否有时间和兴趣?是否还可能与东南亚和本区域其他国家展开联系?
14:16 -【中国就乌克兰局势的反应】
哈斯:让我们谈一下中国的情况吧。有些人,我得承认包括我在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俄乌之战让中国有所省思,美国和它的伙伴们,包括新加坡在内,对俄罗斯的制裁既广且深,也确实是前所未见的。而中国要比俄罗斯更像是一家投资和贸易公司,因此可能更加脆弱。此外,各国所做的其实是在间接保护乌克兰。而正如您所说的,我们所持的战略模糊立场,并不排除直接保卫台湾。
从北京的视角来看,您是否察觉到,中国已有所反思,认清自己在本区域甚至以外,需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因为他们和一场战争有密切的联系?而这是一场被视为是因个人私利而发动的异常残酷的战争。
李总理:我想这让他们面对尴尬,因为乌克兰战争,违背了中国非常重视的原则:领土完整、国家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如果你能这样对待乌克兰,将顿巴斯视为独立个体或可能是共和国……
哈斯:那台湾呢?
李总理:或中国其他非汉族地区?所以说,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从制裁行动也可看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大家有生意往来,在彼此国家互设账户,而任何国家,尤其大国 ,都有可能拆毁他人的房子。我可能拥有很多美国国债,但如果美国决定冻结这些账户,那就会带来实际的经济损失。所以,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切断与中国的联系,认为没中国也无所谓 反正你没在中国的银行拥有同等规模的账户,可是你们的经济是相互依赖的,中国是你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是许多美国公司的制造基地,这些环节一旦断裂,势必也会伤害到你。这并不是说你会陷入很糟糕的情况,但我想双方都会意识到 这么做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点:我不认为在本区域内,中国会因为拒绝与俄罗斯保持距离,而承担什么代价。处在这个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在乎国家主权和《联合国宪章》。但同时也希望与中国维持关系,而其中也有不少国家与俄罗斯也关系密切,如印度。所以,中国如今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并认为你现在反倒来要求他们协助解决俄罗斯问题,而中国的回应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换句话说,你自己的问题请自行解决。
17:52 -【印太经济框架】
哈斯:我们有注意到这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印太经济框架。我有两个相关问题:您认为这个框架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当局已阐明该框架的概念,但还未具体说明其细节。印太经济框架能在多大程度上,作为美国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替代方案?这框架是否会被视为替代品,或充其量只是个不很理想的次佳选择?印太经济框架能或将发挥什么作用?
李总理:印太经济框架应该为美国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定下正面的议程,一个包容和具前瞻性,并能给双方带来好处的议程。最理想的情况是,我们同时也拥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那已是付诸东流。
哈斯:(美国政府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正在摇头。)
李总理:付诸东流。TPP已变成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意味着美国没有参与其中。如今,中国已申请加入,美国打算怎么做?身为CPTPP成员国的我们又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就如何处理这项申请达成一些共识。顺道一提,台湾也提出了申请。美国如果要表明它们参与本区域的事务,又会如何回应呢?
在理想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采取贸易自由化的市场准入方式,与一个无法重新加入的地区建立联系,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但我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下,即使要采取其他方式也太难了,所以美国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
印太经济框架并不涵盖所有美国需要做的事项,但如果能完成这些事项,会带来积极成果。我想说的是,美国可以尽量将印太经济框架变得更具实质性,因此在缺乏自由贸易协定的元素和市场准入的情况下,至少可以考虑纳入一些数码经济合作或绿色可持续经济合作的元素。
我们可以朝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小步前进。除了需要国会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TPA),或需要批准一些法案之外,美国可以开始行动,也许在美国未来的几次选举中,整体情绪改变会使之变得更可行,那就会有一条前进的道路。在这期间,政治是一种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
哈斯:就像我们在地球另一端常说的:“因沙拉!”(但凭真主之意)如果问起人们 说到词汇联想,说起“全球化”,跟全球化联想到一起的国家,新加坡……
李总理:我们名列前茅
哈斯:没错,但现在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词是 “去全球化”,因为有制裁、有约束和央行资产被冻结,因为供应链、冠病和中美摩擦等因素。您对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之间的这种平衡有什么看法?您又有什么担忧?
21:02 -【平衡 “全球化” 与 “去全球化”】
李总理:对我们来说,理想的情况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政治评论家汤姆·弗里德曼以前经常写这样的书,但这世界并不平坦,不仅有丘陵和山谷
还有不易跨越的鸿沟,有些甚至正在加深。我们必须尽可能属于这个世界,最大最平坦最安全的部分,以确保我们能继续维持生计。
我无法预见任何国家走回头路,完全回归到各自为政。要完全只在美国制造苹果手机是不可能的,就像要完全只在美国制造波音飞机一样。国际贸易是有必要的,商业往来也是必须的。我们要有程序,才能确保我们能信赖合作伙伴,同时可以互相依靠,并在出现问题时有冗余保障,但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和经济合作仍必须继续进行。
这其中也存在挑战,那就是要如何讨论重新塑造和重建美国制造业等善意的举措,却又不使这些举措被过度渲染,而成为不赚钱经济活动的代名词。这会导致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美国工人陷入困境,这就是美国所面对的挑战。
对我们而言,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我们仍是可靠的全球供应链的一份子,继续和你们合作,维持良好关系。而你们也能继续信任我们,继续保持商务往来,不光是新美两国,而是有个可发挥“墨迹扩散”效应的更大框架,让更多的国家相互合作,而对那些框架之外的国家,有某种筛选形式,而不是完全把他们排除在外。
因为我认为,如果说你们要和中国切断一切关系,你不但不会打倒它,反而会严重地伤了自己。
哈斯:
我同意您的观点。有时候,我更喜欢“保持距离”这一词,倾向于选择性地保持距离 而不是完全切断关系。在联合声明中有一部分——我们稍后会再接受各位的提问——有关朝鲜的部分,提到大家都熟悉的概念: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持有乐观心态,但我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您认为实际可行的进程是什么?如果无法实现 即便是个长期目标,您认为在朝鲜问题上,实际可行的短中期目标又是什么?
李总理:谁的目标?
24:00 -【朝鲜半岛局势】
李总理:我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我不认为会有哪些政治人物同意朝鲜应该拥有核武器.我觉得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朝鲜会面临吓阻,现状得以维持,但很多国家还是会继续不承认朝鲜,因为一旦承认了,就会造成许多后果。每个人的直接反应将是,既然它有权拥有核武器,还能受他国承认,那我呢?我为何不采取行动?如果朝鲜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却拥有,那就应该受到遏制,这或许能防止核武器继续进一步扩散,这是有可能。
哈斯:但与此同时,我知道您想说的是……
李总理:我不认为朝鲜的做法是疯子的行为,他们看到的是,核武器有很大的威慑作用,所以他们势必不会放弃,无论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政权。
哈斯:您一开始其实就提到这一点。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不管这是不是其中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布达佩斯备忘录》 给予乌克兰安全保障,乌克兰也归还了从苏联继承下来的核武器。但如今,乌克兰已遭受两次侵略,2014年和现在;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也已瓦解成为历史。您是否担心,尽管我们都反对核武器的扩散,但外交政策的很多层面似乎在支持核武扩散?
李总理:我们对此确实感到担忧,但这就是现在的国际局势。
哈斯:在这严肃的基调上,容我开放让观众提问,拿到麦克风后,请道明身份。我可能会来点羽毛球或乒乓之类的玩法,或是匹克球——考虑到在场观众的年龄——我们在观众之间来回进行。
李总理:可别忘了演讲者。
哈斯:有道理,您说得对。萨克海姆,请。
多福·萨克海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理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上次和您见面的时候,我的头发比现在茂密得多。想请问您关于南中国海局势,以及您是否认为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与您所谈到的分裂以及其后果,将对南中国海的局势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认为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会是如何?现状是否持续?或者可会有任何变化?
27:31 -【南中国海纷争】
李总理:我认为南中国海存在着一些事实。各个环礁和岛屿由不同的国家占据
有的填海造地、扩大岛礁、筑防御基地,主权声索相互重叠,错综复杂。中国是主权声索国,亚细安其中四国也是,不包括新加坡。
亚细安和中国一直在进行长期对话,探讨如何处理问题。我们有个《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也正在商议拟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守则。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也有了谈判文案,我们拟定了序言部分,但制定行为守则非常困难,因为要定义问题,就已经是在问题上纠缠了。具争议性的部分是哪些?我的部分可没有争议,你的才有争议。因此,我认为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航行自由是重要的,国际法是重要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重要的,而和平解决争端也是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一些有可能升级的意外冲突或碰撞。
我并不认为声索国会想看到问题走向极端,因为亚细安所有国家都和中国有密切经济往来,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这只是宏观层面的其中一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可以作出一些妥协。我们关注的是航行自由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因为大量的国际贸易都需要经过南中国海,如能源和许多其他物资。说回乌克兰,我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我不认为这与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有何密切关联。
迈克尔·莫塞蒂希(PBS Online 新闻一小时):贵国外长呼吁积极调解,并提议邀请中国来当乌克兰局势的调解者。中国真能充当独立的调解人吗?考虑到中俄关系正日益密切,许多观察者也认为,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不至于太难堪,其实攸关中国的实际利益。
李总理:我觉得你是在引述彭博社报道的一个标题。这篇报道渲染了我国外长的讲话,我并不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30:32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充当协调人?】
李总理:我也不认为中方会自愿扛起这项任务。我认为,他们会宁可由其他人出面,而我也不认为缺乏调解人是乌克兰局势的问题所在。
史蒂芬·比根(Macro Advisory Partners LLC):新加坡是亚洲其中几个重要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如亚细安和亚太经合组织。但印太地区也有许多其他组织,甚至是新的组织,例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不算太新的组织,但肯定在演变,还有五眼联盟,也不是什么新机制,但是个重要平台。
总理先生,我只是想了解新加坡的看法。您是否支持这些组织,尤其是新冒起的组织?您怎么看新加坡的角色?未必是加入,而是您如何看待与它们的关系?
31:40 -【新加坡如何看待全球安全安排】
李总理:我们理解这些新组织成立的原因。美国在本区域有其战略利益,并希望推进这些利益,而美国自然会想要与不同国家组建各个组织,以实现共同目标。AUKUS是个例子,四方安全对话是另一个,五眼联盟存在很长时间了,而这些组织都是政治格局中的一环。
亚细安仍然处在这个格局中。我们谈论过亚细安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亚细安能够凝聚各方力量,扮演有用的角色、促成讨论、召集各方,那么其他各方也都会有各自的位置。但这得取决于亚细安。亚细安有10个不同国家,地缘政治情况和战略观点各异。
所以想让亚细安取得共识并发挥影响力,需要一个过程。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东南亚地区必须拥有一个轴心点来聚拢各成员国,而不是把彼此推开。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把亚细安各国凝聚起来。我刚才提到亚太经合组织,还有东亚峰会,这与亚细安有着密切关系,与会国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和印度,另有印太经济框架。我们希望当这个框架成立后,有朝一日至少会是个具包容性的组织。当你有了这些具包容性的组织,当然其他组织也能存在,这就是世界的规律。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总理先生,我曾好长一段时间在新加坡担任财经记者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海峡时报指数似乎已从冠病疫情的低谷中强力回弹,就像许多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但中国股市包括大陆和香港并非如此。您是否认为接下来,新加坡至少在金融方面,因为更能与中国市场的困难处境区别开来而有所获益?
李总理:不,我们怎么可能脱离中国市场?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或者说 与他们的区别更明显会对你们更有利吗?
李总理:我们和中国市场不脱离 。我们有商业往来,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新加坡有投资,而我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也不少,我们希望他们好。
34:27 -【后冠病经济复苏与中国市场前景】
李总理:许多分析师谈到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都归咎于政策,中国政府的决策。我认为中国想要在科技领域建立一套新规则,而他们认为股市表现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就经济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尽管受疫情冲击,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相当强劲。如果把眼光放远至后冠病时代,我们相信中国是有潜力,继续是个充满机遇、发展中的经济体。我们希望能继续和他们合作。
香港是另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他们正处于过渡期。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市场受中国大陆的影响,也因为香港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也需要时间化解。我们希望他们能解决。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因为香港的种种问题,一些当地的企业或民众可能希望移到别处发展,他们可能想到新加坡来,如果他们想来,我们会乐意接受。
但从更广的角度看,香港萎靡不振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宁愿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一荣俱荣,我们能生存,他们也一样,这并非是二选一的情况。
哈斯:我想就您之前提出的问题,再谈一谈。在美国的外交机构,或者甚至更广的层面来看,大家形成一种普遍的判断,经过数十年努力,仍无法成功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假设美国的希望是让中国的经济更开放,更符合国际规则,政治上更开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不那么强势。但实际情况是,中国选择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并变得更强大,姿态和行为上却并未变得更温和,而这也导致大家认为 我们需要设定更多的限制。您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还是过度解读了?
37:01 -【中国与全球体系】
李总理:我想我们必须整体来看这个问题。中国要发展和壮大,我想这股崛起的动能势不可挡。问题是如何将其纳入全球体系?您可以尝试阻止它,拖延它的进度,这样你也许可以稍微自我保护一阵,但长期下来反而会让双边关系变得棘手。或者,你可以尝试与他们合作,协助他们融入全球体系,他们从中受益,你也可以得益。长久下来,你希望有个建设性的进程会发生。
我并不认为原本的预计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也不是我们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在多方面和中国接触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么做本身有好处,美国的经济、消费者、跨国公司,都因为你们与中国合作而大大获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认为,中国获益了壮大了,你们也获益了,企业也蒸蒸日上,没什么需要改进的。
的确,双方都得利了,可是如今平衡点已转移。过去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 ,如今它在某些领域已发展到和美国一样大,甚至可能更强大,论购买力平价 (PPP) 的话。
过去在政治或经济上可做的调整和优惠,如今已不可行,就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你们必须根据情势调整。
首先,需要逐渐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再只是发展中的国家,而是越来越接近发达的经济体。其次,我们需要给它一些空间,让它可以对国际体系发挥影响。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股份,或对世界银行发挥影响力,你不需要改变现有的整个国际秩序体系或国际规则。这是大家都已经融入的框架,但现在来了个大国 它想要参与,你必须让他们参与。
而如果你拒绝,他们会说:好吧,我大可自己来,我既然没法加入世界银行、拥有更大的投票权,那我就另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会有很多国家想加入。我也会希望和邻国合作,共同开展 “一带一路” 倡议。
原则上,这些都是合乎情理的事,因为这是个大国,你会想和它合作,而双赢的机制是什么呢? 实际上,这会带来什么困难?困难就在于,当一个非常强大的伙伴和一个非常弱小的伙伴合作,他们将很难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
一个大国很难意识到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有多大,即使它并没有这样的用意。而小国要在众多的合作项目与机遇中运行并获益,还要不时接受对方的提议或无法拒绝的要求,这也是很困难的。
墨西哥人有一句话:“不管我们喜不喜欢,美国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就是小国的两难。
Kim Dozier(《时代》杂志):我是《时代》杂志的 Kim Dozier。我想问的是,拜登政府是否接受了您所建议的“北京耳语者”角色,为美国政权做传话者?
李总理:我可不是 “北京耳语者”。
Kim Dozier(《时代》杂志):有这个可能吗?
李总理:不可能。新加坡不是那个家庭的一分子。我们是个以华族占多数的东南亚国家,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有独立国家利益和优先考虑事项。中国是如此看待我们,我们也提醒他们这点。
42:11 -【中美关系与往来】
Kim Dozier(《时代》杂志):白宫和美国国会两党对中国某些做法感到愤怒。他们认为中国窃取知识产权,或投资美国公司后撤回资金,并带走相关技术。新加坡如何跟他们做生意?你们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也是最透明的国家,您会怎么告诉美国国会,中国是可以做生意的?还有怎么做?
李总理:我认为这是两个问题。腐败是其一,窃取知识产权是另一回事 。
我知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公司和其他企业遇到知识产权相关问题。不论是在正式情况下被剥夺了知识产权,或是非正式情况下,这些问题以不同形式出现。
如果你问问这些公司,他们会告诉你问题并未消失,但是变得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中国现在更重视保护本身的知识产权。但我想中国人也非常希望,正如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做法一样,向其他国家学习它们的科技和点子。就像你们从欧洲国家那里获益,通过无数欧洲移民和访客获得了不少点子,也靠自己的渠道悄悄获取信息。中国也这么做。
我想,让美国国会非常不满的是,当人们发现一些盗取技术的人似乎与中国大陆有渊源,但受害者却求助无门,也得不到任何同情。或听说:“我也曾遇到同样的情况” 。你不认同这样的解释,但却无能为力。
针对这类问题,我不认为制裁能产生多大效用。你们需要做的是在高层级进行非常严肃的对话,明确表明双方必须建立互信才能维持稳定的关系。如果一方或双方做了一些破坏两国互信的事,我们可能意见不同,我也可能不喜欢你,但我需要在一定的程度上信任你,才能继续和你做生意,共同解决问题。正如乔治·舒尔茨在他百岁诞辰上说过:“信任是国家的硬通货”。当今世界正严重缺乏这样的信任,这也是为什么知识产权的窃取和网络安全仍是个问题。
46:20 -【应对气候危机】
Kara Tan Bhala (Seven Pillars Institute for Global Finance and Ethics):我是 Kara Tan Bhala,来自 Seven Pillars Institute。我曾是马来西亚人。面对气候危机 您认为新加坡会是怎样的情况,以迄今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世界又会如何?
哈斯:我也想就气候课题向李总理提问。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依赖,导致人们重新强调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您是否担心这会导致人们不那么重视气候课题?您是否会担心我们正失去宝贵时间?
李总理:我对气候变化非常担忧。你问我对应对措施有什么看法。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不足够的。科学家的立场非常明确,他们有礼貌地提出具有冲击力的观点,但他们努力的方向一直比他们的预测更为极端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新加坡非常重视科学家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地势很低的岛国,最高点稍微高过美国华盛顿纪念碑,就这样。如果海平面上升,而这一定会发生,我们不至于会在一夜间被淹没,但会经常发生水灾,像路易斯安那州一样。
新加坡正尽力应对气候危机,但也得取决于全球的努力,因为我们在全球排放量只占 0.2% 或 0.3%。我们必须尽一分力,必须以身作则,希望在本世纪中叶达到碳中和。我们正努力确定能多快实现目标,但这取决于技术和碳交易市场,而这些都是大问号。
此外,这还取决于国际秩序。如果和俄罗斯交战,大家将无法在减排问题上与俄罗斯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分摊碳减排责任。我认为这会是个大问题,即使没有交战,即使与中国之间有对话。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非常努力地和中国保持联系,当两国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就很难取得进展。美国已明确表明,不准备以气候作为讨论其他课题的条件,中方于是说,那何必进行讨论。我认为这将是非常困难。我们将达不到所设下的目标,即使这些目标还不够高。大家应该有所准备。
切断对俄罗斯的依赖,首当其冲的将是欧洲国家。但除非俄罗斯石油从世界上消失,而他们本身没有内需消费,否则这个问题会在其他地方出现。从气候课题角度来看,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从欧洲的角度看,恕我直言,我认为如果没有核能,欧洲就很难实现净零排放,但政治上没人会承认这一点。
50:09 -【新加坡如何因应气候危机】
哈斯:当您指出,缓解危机永远或不太可能奏效时,我不想把话强加在您身上,但我们不能孤注一掷,因为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对新加坡政府而言,在政策方面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意味着新加坡更强调适应气候变化?
李总理:首先在缓解危机方面,我们尽本分,但我们知道新加坡不能决定结果,世界做的也不够多。因此,我们必须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如果我们说的是下来100年,那我就有100年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也有足够的资源去做。
冠病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暴发之前,我曾花时间在常年公开讲话中,向新加坡人阐明气候变化,以及对他们来说为什么重要。我说:你们有100年的时间做准备。如果海平面上升18英寸,甚至是双倍,我们还可以应付。我们可以建造圩田和堤坝,可以填海造地、垫高土地,而我们也有资源这么做。我也说:100年内投入1000亿元是我们能负担的。如果持之以恒,我们就能生存下去。我仍然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会这么做。但我必须指出,100年并非终点,它只是第一个里程碑,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几个世纪。
哈斯:您是否愿意支持相关的研究和实验,支持各项能帮地球降温的新科技?所谓的……
李总理:地理工程学
哈斯:新加坡是否愿意批准一些实验项目?
李总理:我们在这课题上没有官方的立场,但我本身是希望能展开一些试点项目。我认为情况已是非常严峻,和煮蛙效应一样,没有任何政治体系能采取足够积极的反应。因为今天的种种问题总比气候变化挑战更为迫切。此外,依据现有的科技技术和国际框架,也无法制定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方案。如果我们需要进行与地球工程相关的实验,比如在天空中设置一些镜子 甚至是气溶胶,那我们就必须非常谨慎地思考。我们不应该未经深思熟虑,就排除任何可能性。
52:55 -【国与国之间的数码合作】
Sharik Zafar (Meta):我想进一步了解您对数码合作项目的看法。新加坡曾表示希望美国政府能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促进和东南亚的数码合作项目 我的公司总部…
李总理:关于数码合作?是的,我们确实鼓励数码合作项目。我们和新西兰、智利签署了《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中国已申请加入,韩国也要加入。我们正尝试让美国也考虑和我们签署类似的协定。这有必要,因为需要有个框架相互了解,有套规定来讨论可共享哪些信息、在哪里储存信息、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么做是有实质意义的。我不知道这个名称是不是我们首创,不过我们决定后,就大力倡导这个数码伙伴协定,把相关事项纳入其中,将之和传统的自贸协定区分开来。这就是我们希望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推行的事项之一。
哈斯:我认为有人会误解其用意。在这个带有政治风险的贸易环境中,探索数码领域的空间似乎比其他领域更大。
李总理:但即便如此,我认为可能有些敏感之处,因为这样的环境对信誉不佳的科技公司是有利的。
哈斯:我们不讨论这话题,线上还有其他人要提问吗?
55:01 -【缅甸局势】
Kira Kay(Bureau for International Reporting):我曾在2001年在新加坡当过研究生,当时在南大教新闻学,今天很高兴能来到现场。我想问您有关在缅甸发生的内战。我非常感谢您呼吁释放政治犯和落实亚细安五点共识,但新加坡是缅甸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包括与军方所属的企业有贸易往来。新加坡银行也在处理有关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收益。看来化解这场危机,除了维护人道主义,新加坡也能从中获益。那么,我们在制裁行动上,还可以期待新加坡做些什么呢?
李总理:我认为在缅甸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对缅甸国内发生的事情能起到巨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缅甸国内的局势,由其国内因素所导致。军方与翁山淑枝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之间存在深层的冲突,而且持续了几十年。你说新加坡在那里有投资项目,事实上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的人都想离开,却被困在那里,既不能卖掉公司,也没法离开。我们的银行在处理缅甸的账目,有些是我们指定的,有些则是我们在密切留意的。一旦情况有变,我们的银行将会提交可疑交易报告,我们就会介入调查。
你也很清楚,以银行账目作为战略,迫使一个国家改变政策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像缅甸这样一个国家,更乐于自我封闭,与世界切断联系。因此,我们没有办法采取太激烈的措施来应对,只能继续尝试和缅甸军方保持沟通。我们上一次这么做,也花了很长的时间,但只要有耐心,缅甸最终还是回到正轨,举行了大选,选出人民政府,这个政权也维持了一段时间。我们也许有必要再这么做,但我希望这一次不会更加困难。
哈斯:总理先生,我们要感谢您今天不只拨冗出席这场对话会,还非常开放坦诚地和我们分享了新加坡以及全球各地面对的种种挑战。我们期待再次在这里与您见面。祝福您与您的代表团,还有新加坡人民一切都好。谢谢您!谢谢!
李显龙总理:希望中美双方坦白坦率坦诚讨论分歧矛盾 扭转关系走向
文 / 韩咏红
4/02/2022
(早报讯)亚太地区持续了50年的和平局面不能视为理所当然,中美关系是区域和平的重要因素。为此,我国总理李显龙呼吁中美“坦白、坦率、坦诚”地讨论分歧或矛盾,逐步扭转双边关系的恶化走向。
在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一个月,国际关系紧张之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各方瞩目下对美国进行访问。他行程中多次谈话的内容,反映出此行访美非选边站队,而是希望鼓励各国在多边合作的共同架构中沟通,避免走向冲突的不归路。
继在美国华盛顿与政要和智库进行会谈,再续程前往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后,李总理当地时间星期五(1日)在总结此行时指出,类似俄乌战争的冲突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发生,过去50年来让各国稳健发展、和平竞争的亚太地区和平是否能够维持,也“非常难说”,不能视为会自然产生。
他强调,各国能否在一个框架下发展与竞争,这个问题比各国之间竞争力的高下更为重要。亚太地区需要超越眼前的乌克兰危机,思考如何在亚太地区推动事态与机制的发展,来避开走上阻遏完全失效、类似于俄乌战争的冲突在本区域暴发、人命牺牲的结局。
李总理指出,他此行中在记者会、在智库论坛中谈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峰会,以及美国政府正在讨论的印太经济框架,都是让区域国家扩大合作领域与提升相互依存的机制。
他说:“与此同时,提供平台让大家讨论一些相当困难的问题,避免这些问题演变为不可能处理。新加坡在尽一份力来鼓励这一点,但这需要很多的参与者。我们也利用我们有的影响力来鼓励其他参与者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是我来美国的原因之一。”
李总理也谈到,乌克兰课题出现在他与美国政府高层、银行家以及老朋友的谈话。美国人正在超前思考战争可能的结果、如何处理这些结果,尤其是如何处理乌克兰危机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李总理形容,中美关系的问题已经“让人忧心忡忡”。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从拜登政府上任才开始,而是在好几任美国政府中逐渐恶化。
他认为,中美之间存在沟通渠道,但这些渠道恐怕还不足以应对中美之间需要讨论而又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政策方面,由于缺乏互信,美国政府、国会以及民间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在某方面一直延续着,问题难以克服。
他说:“乌克兰战争肯定会影响中美关系,我相信中美两方都不希望他们的关系会因为乌克兰而恶化,所以我希望双方都能保持沟通联系,坦白、坦率、坦诚地讨论他们之间的一些分歧或矛盾,逐步扭转他们关系的走向。”
李总理是在上个星期天(当地时间3月26日)飞抵华盛顿,在公开活动中,他分别会见了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国防部长奥斯汀、财政部长耶伦、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资深众议院议员,并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出席一场对话会。他过后也到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他说:“我告诉他们我的观点,也很有兴趣聆听他们的看法。我希望情况有可能逐步转向对的方向。”
他希望中美能够维持长期稳定的双边联系,让全世界,尤其是新加坡也能够受益,能够照顾本国人民民生和新加坡的未来。
李显龙一行将在当地时间4月2日返回新加坡。
李显龙总理:中国不会因不疏远俄罗斯而在区域内付出政治代价
文 / 韩咏红
3/30/2022

(早报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让中国面对尴尬问题,因为这违反了中国本身珍惜的领土完整、主权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不过,在亚太区域,中国不会因为拒绝疏远俄罗斯而付出政治代价。
我国总理李显龙当地时间星期三(3月30日)出席华盛顿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会,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主持时问到,中国与战争发动者的关系如此密切,俄乌之战会否让中国省思,并且在区域内付出政治代价?
李总理认为,乌克兰的情况给中国出难题,如果可以这样对待乌克兰,东南部的顿巴斯可以被当作是飞地,那中国国土上非汉族的聚集地呢?
至于制裁的问题,总理则从世界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大国采取制裁措施会导致另一个国家面对实际的经济后果,但是换个角度,如果美国切断中国的联系,以为反正自己在中国没有相等规模的存款,但实际上两国的经济密切相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许多美国公司的生产基地。切断关系反过来也会伤害美国。
他说:“这不等于说你会落入很糟的状况,但是我认为两边都知道这么做的代价会非常高。”
至于区域其他国家,李总理说:“本区域的所有国家,都担心主权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保持和中国的联系,而且有的国家与俄罗斯也有重要联系,印度就是一个例子。”

他说,事实是中国采取了自己的立场,而中国认为他人在请求中国帮解决俄罗斯造成的问题,中国给的回应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李总理解读:“换言之,你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在一个小时的对话会里,主持人、台下与线上观众提出的问题中,不少围绕着中国。
总理在回答另一个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时也说:“如果你说你打算把中国完全切割出去,你打不死它,而你自己也会受重伤。”
他对这群华盛顿观众重申,中国发展的动力巨大且不能阻挡,“你可以尝试阻挡它、拖慢它,这样你可以为自己阻绝一些冲击,但也设定了一个会持续很长时间的麻烦关系。你也可以尝试和它合作,让它融入国际体系,你和它都从中获益。慢慢的,你希望一个建设性演变会发生。”
随着更多提问聚焦中国,有美国媒体记者问:美国总统拜登和国会是否接受了李总理提供的“北京耳语者”(Beijing whisperer)角色,意即能和北京沟通的人。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世时,也经常被问起是否扮演“传话者”角色的问题,他都否认。

在华盛顿的李总理听到这个问题时也立刻回答:“我不是北京耳语者”。该媒体记者马上跟进问:“你能当吗?”
李总理笑着解释,新加坡不是(中国)家庭的一员。新加坡作为以华族占多数的东南亚多元种族国家,有独立的国家利益和优先考虑顺序。“中国以这个定位对待我们,我们也提醒他们这点。”
谈到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辩论,李总理认为各国不可能走回头路,大家仍需要国际贸易,但也需要设立机制来确保伙伴间的互信,并且留有冗余以预防贸易线失效。美国需要把制造业带回国,同时避免导致保护没有经济效益的企业,新加坡则要确保自己是可靠供应链里的一环。
李总理以“墨迹扩散“效应来比喻世界各国可以相互合作,但又有某种过滤作用,能避免完全与某些国家切割。
全球化、多边合作框架、让对手在同一个框架里互动,是李总理一再强调的概念。在对话开场谈到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负面冲击时,李总理就指出,这场危机让各国共同应对贸易、气候变化、疫情预防、核不扩散的多边合作机制难以运作。

他说,世界不再有一个能让对手、敌对方、竞争者合作的机制,而这原本正是大家创造共赢的机制。李总理说:“现在是要分出输赢,你要把对方打倒、修理他、摧毁它的经济,这样其他国家要如何继续合作,而不沦入无序、自给自足或无政府状态?新加坡非常担心这一点,因为我们需要全球化维持生计。”
语录

“如果你跟一些(美国)公司谈,他们会告诉你问题依然存在,不过也已经变得比较可控。因为中国现在也有更大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我认为中国希望从其他国家得到的,就如美国在19及20世纪初非常努力做的一样,就是从有这些技术和想法的国家,汲取他们的技术和想法。正如你们过去也从欧洲学习,从不少带着想法、来自欧洲的流亡人士和访客中得益。有时候你们也通过自己静悄悄的渠道获取这些信息。中国人也在这么做。……对于这个课题,我认为制裁不会很有效。需要做的是与他们非常高层的人进行非常认真的对话,很清楚地让他们知道,要维持稳定的关系,双方必须有互信。”
——李总理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会上回答关于美国国会对中国剽窃知识产权充满愤怒的问题。
“我想我们都希望看到台湾的现状能维持,如果有变化也不是以暴力或非和平方式发生。但这很难处理,因为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战略问题,而涉及到政治和当地民众的感情。因此,你只能通过很长的时间去处理。”
——李总理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会上谈到台海问题。

李显龙总理谈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
文 / 黎康
11/19/2021
李显龙总理星期三(17日)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的晚宴上,接受了彭博社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的访问。
在长达45分钟的对谈中,李总理回答了关于国际形势、冠病疫情和新加坡相关的多个问题,尤其是就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问题展开了20分钟的交流。
中美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如何看待“东方崛起西方衰落”论?台海局势又是否一触即发?点击视频,听李显龙总理回答。
以下是文字实录:
米思伟:总理,如同迈克所说的,非常感谢你让我们来到这里,也感谢你再次与我对话。
李显龙:感谢你来,也感谢你再次组织这次对话。这是我们的第四次或第五次了。
米思伟:我想我们从国际形势开始,然后再具体谈冠病疫情以及新加坡。首先,中国和美国,今年早些时候或去年年底,你曾呼吁休战。我想知道,过去一周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上看到了关于气候变化的协议,现在看到了习近平和拜登的谈话,这算得上是你呼吁的休战吗?
李显龙:我认为这是个必要的开始,两国之间的分歧多且深。分歧并不局限于个别课题,而是涉及到基本的思维方式。这不是一场会议或一份协议就能解决或缓解的。但美国和中国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达成一些共识是好事。两位领导人能够举行这次视讯会议并坦率交谈,也至关重要。
米思伟:你如何描述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你看到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李显龙:这两个国家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不一样,看待彼此的方式也非常不同。对美国人来说,中国不仅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是一个挑战者以及一个严重的问题,几乎是一个对手,这已成为两党非常强烈的共识。我不是说行政部门都是这样想的,但我认为这是美国社会的普遍看法,至少智库是这样想的。
与此同时,与中国的关系不仅是对抗性的战略平衡问题,它还涉及道德层面——对与错,我维护民主,你不是,我是人权,你不是。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定义问题,要过渡到谈共存,谈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变得很困难。
在中国方面,我认为他们的许多记者和民众都有一个已经固定的观点,我想象一些领导也是一样,就是美国要拖慢中国并阻止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后曾经帮助中国,给予他们永久最惠国待遇(MFN),允许他们加入世贸组织,促进了投资增长,让他们变成今天的样子。
第二点,他们有一种感觉,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将在世界上占据应有的位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以何种方式在世界上占据你应有的位置,作为一个非常大的玩家为许多不太大的玩家留出空间,这是一种敏感度和艺术,而它不是与生俱来的。
米思伟:你描述的这种有问题的思维方式,是否也涉及中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美国的时代即将逝去?
李显龙:是的,也有那方面。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东方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美国尤其是一个衰落的大国。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可以了解什么让他们这样想。其他人有时也会这样想。但如果你从长远来看,你真的必须押注美国会从它对自己做的事情中恢复过来。
米思伟:我们可以看看它现在对自己做的其中一件事情吗?我们早些时候在会议上听到了雷蒙多的谈话。她在这里,非常卖力地推销美国印太经济框架。这是没有贸易协议的贸易协议,背后没有贸易协议。我猜想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会更希望现在称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能重启。美国在推销一个你们很难自然就倾向的概念。
李显龙:这些都是政治现实。《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原本是理想的作法。美国花了一些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去决定这就是它希望与这个区域接触的方式,并推动这个旗舰性的实质性项目,它将不仅展示而且实际上深化美国与亚洲的接触和关系。
奥巴马亲自采纳了它。他花了很多时间推动领导人并使谈判取得进展。但我认为他没有做到的,也许就是不可能做到的,是在国内和国会中给予足够的推力。最后,他的时间不够了,不可能透过国会跛脚鸭会期将它夹带通过。反正,希拉里(克林顿)也不认同,当特朗普获胜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而现在处于它已死的位置。我不是说它不能复活,但复活不会在三天或三年后发生。
所以,如果不能这样做,美国还能做什么?好,你仍需要以实质性的议程参与,而如果我不能,我可以谈数码化合作、绿色合作、人力资源合作。虽然缺了一块,但至少我不会在互动中缺席。
米思伟:你从一个卖家的角度非常热衷地谈论发言,但你其实是买家。你是必须决定它是好是坏的那个人。你是否还觉得它有用?
李显龙:它可以是有用的。我们正向美国以及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些成员国提出数码经济协议的想法。我们希望美国能参与其中。要民主党政府这么做并不容易,因为该政府上任时答应要照顾美国的中产阶级,所有事情都需要与此有联系。其实,所有事情最终都会与此有联系,但如果你坚持要立即和直接联系,那你或许会错失很多间接但有价值的计划。
米思伟:中国正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台湾也是。你如何评估其中一方或是双方加入的机会?
李显龙:《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构建方式,欢迎任何愿意、且达到该协定相当高门槛与符合其精神的国家加入。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构想下,我们就设想有一天中国会感兴趣,而中美同处一个TPP框架,将比两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来得更可能。我认为双方都逐渐想通,连最初不以为然、认定这个协定就是要针对自己的中国,后来也决定研究它。他们考虑了很久,终于说或许我们应该感兴趣。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人如今已不在里头了。
从经济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理性的。从程序角度来说,CPTPP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后才能做出决定。当他们在考虑时,考虑的就不只是经济层面,也会有政治考量,战略和安全因素,以及其它任何他们或许正在讨论的双边关系问题和关注。
米思伟:而南中国海也是其中一部分……
李显龙:南中国海不是贸易议题,但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或CPTPP成员国与中国之间也有贸易议题。我希望他们能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更多贸易要比少贸易来得好。我仍相信这点,尽管现在已不太流行。我希望这些事情获得解决的方法,能促进稳定和各国的整合。
米思伟:新加坡一直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施惠者或受惠者。今早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王岐山(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致辞,他提到多边和多边主义大概有20次。这个新的中国,带着礼物向你走来,承诺他是多边主义者。你相信吗?
李显龙:我认为他们说了正确的话,也尝试在做正确的事。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国说出我是一个单边主义者,你会觉得不对劲。他们声称是多边主义者,也想加入所有这些组织。事实上,他们希望投选一些自己人领导这些组织,一些联合国的组织就出现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中国)想影响这些组织的条规,这都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已是一股可观的力量,他们要在世界上有相应的影响力。问题是,当一个非常主要的势力加入一个组织时,你要如何让该组织真正饯行多边主义。原则上,根据各国无论大小和平共存的五项原则,我们都是平等的,但在联合国的实际操作中,大家都知道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平等。
米思伟:这就是说,房间里出现了一头大象。它可能比其他所有伙伴要大得多。
李显龙:是的,而且你必须与这个力量互动,它也需要对自己的运作方式有些自我意识,确保获得大家的接受,从而可以在不动用赤裸裸武力的情况下延续影响力。
米思伟:中国是否已达到这么考虑问题的境界,让你能想象他们坐在你身边,并差不多平等地对待所有人?
李显龙:没有强权平等对待所有人,但有些会做得比其它好些。
米思伟:他们做得更有礼一些。
李显龙:不,我不会说更有礼些。看看美国人,他们从二战结束后就待在亚太地区,在那之前已在菲律宾。七八十年后,依然受到这个地区的欢迎,而不是被视为丑陋的美国人,这说明了一些什么。
米思伟:如果中国加入CPTPP或没加入,会怎么反映出美国在这一区域的角色?
李显龙:如果中国加入CPTPP,美国在这一地区仍有角色可扮演。你在这里有投资、贸易、利益、朋友和盟友。我们希望在(美国)遍布全世界的关注事务时,你有时间经营世界这一部分,吱声不大,却有价值和有经济回报的关系。
米思伟:如果你是乔拜登,你会做什么来改变这个平衡?你说的一切,听起来你认为美国需要为这个区域投入的比现在稍多些。
李显龙:首先,我会尝试推动贸易。你不能签订自贸协议,但你会想推进贸易,尽管民主党的规则不允许。其次是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如果这个关系搞僵了,这个地区每个国家的处境都会变得更难。第三,不要止步于与中国发展关系,而也要经营你在这个地区的其他朋友和盟友。第二部分拜登正尝试在做。这是一段漫长旅程,但他已开始。朋友和盟友,他采取的方式相当明确,我认为人们都相信这点。他可以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确保2024年之后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哪个政党,也有和他相同想法。
米思伟:这非他力所能及……
李显龙:可惜的是,这非他力所能及,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你必须能放远目光,因为美国的利益远远持续到2024年之后。
米思伟:关于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台湾。对于台湾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多担心?
李显龙:我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我不认为战争会在一夜之间发生,但这是一个可能出现意外或误判、需要细致处理的处境。有关国家都说对的话。上午的视频峰会上,拜登说,美国将坚持它的一个中国政策,他也提到了存在很久的台湾关系法。习近平则说,我们并不急于解决两岸问题。这是一个暗号,但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在台湾,蔡英文博士说,我们呼吁各方维持现状。所以,每个人都说对的话,但如果你观察正在发生的事事态的发展,会发现情况并非静态。美国已显著提高与台湾的外交、甚至军事接触的能见度、级别和强度。
中国大陆一直在测试台湾的防空能力。大陆几乎每天都派遣飞机飞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些飞机没有进入台湾的直接空域,但大陆是在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并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在五年前或好几年前,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对台湾有些让步。在台湾方面,本届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两岸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并说,不,这不是一个可接受的构想,并采取了其他行动,例如,在他们的护照上,用英文印上“台湾护照”的字眼。
这些行动都引起了猜疑、紧张和焦虑,导致误判或意外更有可能发生。而且真的,你需要后退一步,“降温”这个词太强烈—冷静一点,想想如果你尝试了另一个选项后,你将有多后悔失去这个选项。
米思伟:你真的认为大陆是这么想的吗?你认为大陆会不会,当然、如果另一个选择是大陆控制台湾?
李显龙:不,我认为如果大陆相当清楚局势是稳定的,如果事态不会逐渐朝着不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他们也许会更放松、慢慢观察事态演变。难点是,如果他们担心情况是往渐渐远离他们的方向发展,不是在经济层面上的离开,因为在经济层面上,我认为大陆将成为台湾经济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而是就台湾人民的态度以及国际环境而言。那么他们可能会判断,如果迟些,事态会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我认为这并不是大陆想马上解决的问题。不过我应该如何处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有香港这一个棘手的问题了。
米思伟:你提到了香港,我们就很快地谈一下。你认为香港是一个大陆增加管线权的地方吗?哪里的限制已经收紧了。
李显龙:我认为,根据香港在去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很难想象这种情况能持续到2047年,到50年。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这样治理这样一个地方。法律无法通过;政府的令状无法执行,而且有蔓延到越过一国两制边境的风险。所以,他们现在的情况是,问题被很坚决地压制了。我认为国际上,甚至是香港内部,都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也认为他们(中国)将从这里观察事态的演变。我不认为他们希望或寻求让香港变得与其他大陆城市一样。这将使得香港对大陆而言没有价值,因为大陆已经有许多繁荣的城市。香港是不同的,所以有价值。不过,在不给一国两制的另一端构成不可容忍的问题的前提下,香港能够有多不同,这是难点所在。
米思伟:香港损失了多少,新加坡得到了多少?
李显龙:我想有些人可能会决定他们更喜欢待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另一边,但是总的来说,我毫不怀疑,如果香港繁荣,新加坡和香港做生意、竞争,新加坡得到的会更多。
新加坡防长:台湾问题是“深红线” 美国应远离
来源:瞰天下
11/05/2021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在第12届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说,台湾问题是一条深红线。他事后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重申,各国应该远离这条深红线,因为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
Nov 3, 2021
到美国华盛顿参加第12届阿斯彭安全论坛(Aspen Security Forum)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当地时间11月3日(本地时间4日凌晨)发表他此行的主旨演说。他过后回答主持人阿斯彭战略集团联合主席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提问时,提出他对台海局势的看法。
约瑟夫·奈问黄永宏是否担心美国目前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以及过程中是否可能出现形势误判的情况。
黄永宏回答说,误判的情况可能发生,这是一条深红线。“若为了台湾动武,我想到时无论是什么局面都不会有赢家,所以我的劝告是应该避而远之。”
他事后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重申,各国应该远离这条深红线,因为靠得太近就会有误判形势的可能。而一旦动武将各方皆输,不仅是美国和中国,东南亚甚至是全球都会陷入混乱。
Nov 3, 2021
马凯硕: 西方不应错误地认为中国需要照搬其模式
10/19/2021
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昨天(18日)说,西方认为中国应该照搬其模式,这是错误的假设,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加强韧和更加自信的文明,而西方亟需明白这一点。
根据中新社报道,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的马凯硕在接受德国“中国平台”网站专访时说,一个崛起的中国并不会步美国的后尘寻求称霸,因为中国专注于改善本国14亿人的生活,而不是卷入毫无必要的战争。
Jul 1, 2021
Kishore Mahbubani of the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former diplomat says U.S.-China tension regarding China’s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may lead to a war.” He says pushing China into a corner would be unwise.
谈及西方国家习惯于将美国视作“民主伙伴”,而将中国视作“挑战和威胁”,马凯硕直言,这种观念并不正确。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其历史上有超过4000年的时间是领先世界的,只有近代以来才有200年左右的时间落后于西方,但后者只是很短的时期。他说,西方认为中国应该照搬其模式,这是错误的假设,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加强韧和更加自信的文明,“西方亟需明白这一点”。
马凯硕认为,关于“新冷战”的表述是错误的。在美苏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相互隔绝,而今天的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当前的确存在大量的地缘政治博弈,但今天的世界已是相互依存的状态,需要共同应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例如冠病疫情和气候变化。
马凯硕强调,一个崛起的中国不会步美国后尘。他认为,中国不希望以一种“传教士”的方式去改变世界,更不会让自身陷入类似伊拉克或者叙利亚那样毫无必要的战争当中,“这是因为中国要专注于改善本国14亿人的生活,这已经够忙了。”
Sep 23, 2021
谈及对下届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期许,马凯硕表示,情绪化是处理地缘政治时最大的误区,德国应该避开这一误区,“过去十年间,中国市场增长了三倍,你不应忘记你的汽车正在销往何处。”
马凯硕曾作为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他的最新著作《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近日被翻译成德文出版发行。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维系新中关系窍门 是要保持有用但不被利用
来自 / 联合早报
文 / 杨浚鑫
10/12/2021

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日前上澳洲访谈节目时,被问及是否对澳中关系出现波折感到惊讶,他以分享新加坡的经验做出回应。“维系与中国的关系在于保持相关性,有用处却不被利用。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须要找到的微妙平衡,新加坡找到了。”
新中关系的维系,在于我国通过政府间合作项目等方式,对中国保持相关性,有用处却不被利用。外交部长维文医生说,这是各国须找到的微妙平衡。
由澳大利亚前国防部长派恩(Christopher Pyne)主持的访谈节目《环球焦点》,前天(10月10日)在澳洲天空新闻台(Sky News Australia)播出第一集,邀请到维文担任嘉宾。
根据外交部提供的访谈文本,派恩就澳中目前的紧张关系询问维文,是否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出现波折感到惊讶。维文回应时强调,他没有资格告诉澳洲如何施展外交,他能做的只是分享新加坡的经验。
维文说,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自2013年起也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因此,从新加坡的角度,我们有着切身利益,而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向来是展示我国的相关性。”
他举出三个新中政府间合作项目,即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以及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其中,重庆项目下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将通过新加坡连接中国西部和东南亚。
维文说:“维系与中国的关系在于保持相关性,有用处却不被利用。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须要找到的微妙平衡,新加坡找到了。”
他强调,新中关系极佳,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不仅上个月访新,两人过去12个月也面对面会见了约四次。“双方互动水平和节奏向来很高。或许较鲜为人知的是,即使在冠病疫情期间,双方仍在关键时刻彼此低调相助。”
长期关系必生分歧 维文:出现时须解决
维文说,新中关系并不对称,因为新加坡太小了,也不是基于完全一致的立场,因为这不可能,但两国找到合作方式,并在出现分歧时共同解决。
他认为,分歧是任何长期关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必须去处理。“这如同一场每周都有同样玩家围坐一桌的游戏。即使你有分歧也要去解决它,并理解这其中有大的格局和更长远的角度。”
派恩进一步追问,新加坡的做法是不是亚细安国家普遍采取的做法。对此,维文说,亚细安已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种贸易相互依存关系是真实的,并仍在增长。”
就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而言,东南亚对此的主要兴趣在于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连通性方面的投资。可见,双方的中长期利益有明显交集。
因此,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东南亚声索国存在分歧和争端,但这只是双方广泛关系中的一个面向。维文说:“没有人希望情况失控或破坏关系的长期轨迹。”
他坦言,领土声索可能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解决,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但它不是各国继续往来和建立关系的绝对障碍。这正是东南亚目前的情况。
维文也重申,亚细安坚持维护包容开放的区域架构。这当然牵涉美国。事实上,美国在东南亚的投资额,超过它在印度、中国和韩国的投资总额,因此在本区域拥有切身利益。
“我曾对美国历届政府说:‘你们已经占得先机。美国仍是东南亚最大的外资来源国。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受到欢迎且具建设性。不要失去这个领先优势。’”
派恩也问维文,是否认为北京正在制定一个能允许澳中有尊严地走出目前混乱局面的方式。对此,维文说,中国在地缘战略上有长远和开阔的眼光,他相信有这方面的计划,虽不清楚何时发生,但希望两国关系能早日改善。

北美法律公益讲座安排
时间:周二到周五 晚间
5:30-7:00(西部)
8:30-9:30(东部)
周二: 遗嘱和资产传承(蒋律师&Joanna)
周三: 数据泄露和个人身份保护&事业机会说明会
周四: 婚姻和家庭法(主讲周律师)
周五:企业法律问题公益讲座(主讲人:蒋律师&Joanna)& 事业机会说明会
Zoom 6045004698,
密码:进群获取

Transcript of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Dr Vivian Balakrishnan’s Interview on Sky News Australia’s “Global Focus with Christopher Pyne” on 15 September 2021
10/12/2021
Christopher Pyne (Sky News Australia): Hello, I am Christopher Pyne, and this is “Global Focus” on Sky News Australia. Today, my guest is Vivian Balakrishnan, who is Singapore’s Foreign Minister and a good friend to Australia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Vivian, welcome to the show,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with us.
Minister: Thank you. Always great to see you. A blast from the past, and we have been up to a lot together.
Pyne: That is definitely true. I am sorry we cannot be together in person. But you know, it would not be too long before we can be again.
Minister: Hope so, hope so.
Py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is clearly strained at the moment,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Does it surprise you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taken this turn?
Minister: Well, first I would say, I am not really in a position to advise Australia. But what I would say, shared as a perspective from Singapore – this tiny city-state in the heart of Southeast Asia. The biggest success story in the last 40 years really has been China after the reform started by Deng Xiaoping. As a result of that, and especially the last 20 years since they joined the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China has become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But the other surprising fact, perhaps, may be that Singapore is also the lar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China, has been since 2013. So, the point is that from a Singapore perspective, we have got skin in the game. And our attitude to China has been to demonstrate relevance. For instance, we have got three Government-to-Government projects. The first one was in Suzhou. It was an industrial park – bring in foreign companies, build manufacturing plants. Second was in Tianjin – that was an eco-city, when this whole th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e about. Our most recent project was in Chongqing – in a sense, part of the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ut really an attempt to connect Western China and through this new corridor which we call the “Chongqing Connectivity Initiative-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Trade Corridor”. This corridor links Western China through into Southeast Asia via Singapore. So, it has been about relevance, about being useful, but not being made use of. This is a delicate balance which all of us need to find, and we have been able to find that. Right now, if you were to ask me, I would have to say our relations are excellent.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was just in town. I have seen him personally face-to-face about four times in the last 12 months. The level of interaction, (and) the tempo has been high. Perhaps the lesser-known fact is that even during this COVID pandemic, at critical moments, quietly, both sides have helped each other at critical points in time. So,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not based on symmetry – you cannot, because we are so small – not based on complete congruence – it is not possible – but we find ways to work together and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we work through them. The point is that you have to treat the issues as they come up – the differences as part and parcel of a longer-term relationship that has to be managed. It is like a game in which the same players are going to be at the table week after week. Even if you have differences, work it out and understand that there is a much larger account and a much longer-term horizon. That is just my take from Singapore. I am in no position to tell Australia how to conduct foreign policy. Julie Bishop and Marise Payne are more than capable of doing this.
Pyne: Yes, indeed. My former House mate in Canberra for 20 years, Marise Payne, would not be appreciative at all of you giving her advice about how to manage our relationships. But she likes you very much.
Minister: She does not need my advice.
Pyne: I know how well you get along.
Minister: We get along perfectly.
Pyne: I have been in some of those meetings of ministers for trade, defence, and foreign affairs, and I know how close you and Marise are. This is a great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got.
Minister: Chris, you have been there. You have seen it up close.
Pyne: I had, and (I) enjoyed it too. The approach that you have just outlined that Singapore is taking with China, is that generally the approach of the ASEAN nations? That they all see similarly that they can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does not have to exclude others?
Minister: Well, I would characterise the relationship with ASEAN and China along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First, China is now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for virtually all of us. But a more recent development which may not be fully appreciated yet, is that if you ask China who thei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is, in fact, ASEAN has now overtaken the EU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S (United States). This trade interdependence is real, and it is growing. So that is the first point. The next point is that even if you look in term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signature project, the key interest of Southeast Asia is investments, and particularly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in connectivity, and still there again you see that there is an obvious confluence of interests – medium and long term interests. Are there problems or differences? You know fully well that there are. For inst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ces over claims, for each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 claims – and I would exclude Singapore because we have no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but for each of the claimant states, their differences, their disputes – even if you want to call it that – with China are just one dimension of a much broader relationship, and therefore would be looked at strategically. No one wants them to get out of hand or to disrupt the long-term trajectory of relationships. Now, one final point I would make about ASEAN, is that ASEAN is very insistent on maintaining an inclusive and open regional architecture. This is something which Australia would be familiar with because you know that we have always been advocates, champions for Australi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with our part of the world. (The) same thing applies to China. Even as China is our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even as China i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vestment, and we are key investors into China, we want to keep our region open, inclusive, and that of course relates to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 America, which has in fact, invested more in Southeast Asia than America has invested in India, China, and (Republic of) Korea combined. That is another fact which is not fully appreciated – the amount of skin that America has in Southeast Asia. I used to tell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You have got a head start. You still remain – when I say “you” (I mean) America – the biggest foreign investor in Southeast Asia. You are a welcome, constructive presence. Do not lose the head start. You are welcome.” So, the key word there is inclusivity. We want Southeast Asia to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with America, with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of course, you have got Japan, (Republic of) Korea, and India, and that in a sense, creates the larger outer arc. Another example of that is the RCEP,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The only one that could not get onto and sign was India. But for 15 countries – and the combined economy is a huge big chunk – to get on this platform, and to get on at a time when there is a pushback globally against free trade and economy integration, makes it all the more significant. So I would say it is a big, deep, and evolving account. But Australia is part of this account too, and tha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se, especially back home for you.
Pyne: Yes. Well, it is interesting because here in Australia, the media commentary is very much the only issue that people talk about is the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nations in the Indo Pacific,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s you know, often used as the primary example of tension. But what you are saying, if I could paraphrase, is that the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Brunei, Indonesia, Malaysia, (and) others that have claim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see that as just one part of a multi-faceted relationship with, what is clearly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region, and 1.3 billion people who are not suddenly going to go away. So, managing that relationship and that South China Sea tension is just another thing to discuss, as opposed to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lationship.
Minister: It is a long-term game. You are not dealing with an adversary, (and) you do not want to make them (an) adversary. But it is a stakeholder. You will have differences, and there will be divergence. The question is, can you resolve it? Even if you cannot (right) now – frankly territorial claims are very difficult to resolve; it may take years, decades even, and no country is going to walk away from claims lightly. But it does not have to be an absolute block to ongoing engage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those relationships. So that is really what is happening in Southeast Asia.
Pyne: Do you think that there is a party, and you cannot also comment on foreign policy out of Beijing, but would it surprise you if there was not a group in Beijing formulating, now, a dignified exit for both Australia and China out of the current imbroglio that we find ourselves in?
Minister: China thinks long term and takes a wide view in geo-strategy. I am sure there would be a paper somewhere in a drawer on what happens when we press the green button and say, the sun is out and it is (a) good day mate. When that will happen? I do not know. But I hope it happens soon.
Pyne: Yeah, me too. Well, Vivian that has been great. We have to go to a break now, but Sky News Australia will come back after the break and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It might switch to the role of the US in the Indo Pacific. So, thank you very much so far,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again in a couple of minutes.
Christopher Pyne (Sky News Australia): Welcome back to Global Focus here on Sky News Australia. My guest today is Vivian Balakrishnan, Singaporean Foreign Minister.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ASEAN, Singapore, Australia, the role of China in our region, and now we will shift to the other great superpower in the Indo Pacific, which is the US. Vivian, the Afghanistan war has effectively come to an end, Taliban is back in power in Kabul after 20 years. I know you cannot speak for all of ASEAN, but you can speak for the Singaporean Government. Is it your view and Singapore’s that this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US completing its mission and now extricating itself from a very difficult conflict or is it being seen as a significant defeat for the US, which is going to take many years to recover from in terms of their prestige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Minister: That is a profound question. Actually, both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and you would be familiar with this, wer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SAF) in Afghanistan. Why did America go in? And why was Australia and even Singapore part of the ISAF? It was because of terrorism. In fact, more specifically because of 9/11. In Singapore’s case, we even discovered a local terrorist cell. Fortunately, we discovered it before they could actually take any action. But even this local homegrown cell had links with Al-Qaeda. So we fully understand why in the aftermath of 9/11, America had to go in (to Afghanistan). The question then is, is this threat from terrorism resolved? The answer is that it is certainly acute. (The) immediate threat 20 years ago was settled, but the nature of terrorism has now metastasised and (is) turbocharged with internet technologies. In fact, the risk has gone up, not gone down. But really, if you think, and here we put ourselves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shoes, the truth is they inherited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Actually, they are not the first Administration to want to come out of Afghanistan. So, they were in a difficult pickle and I think you, as a former Defence Minister will know as well as I do, there is no easy, neat, tidy way to get out of a sticky situation like that. So, we understand why they had to get out. Of course, everyone wishes it was done more elegantly, but that is more easily said than done. We hope Afghanistan will not become another haven for terrorists again. But we have no illusions; I think both in Australia and in Southeast Asia, we have got homegrown terrorists. We have got terrorists in our own region.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y will be activated or at least enthused by current events in Afghanistan to try their luck. So, we will have to be vigilant. That is what confronts us. As far as the people in Afghanistan is concerned, I think there is an emerging humanitarian disaster. We hope that the Taliban leaders – you know, 20 years is a new generation – we hope that they will take good care of their own people. We hope that they will also build funct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neighbour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ut time will tell. In the end, I think the other point is that Afghanistan has always been the graveyard of empires. The British discovered it, the Russians re-learnt it. It looks like Americ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there has been another footnote in history of this recurring pattern. So, there we have it – a difficult situation. We have great sympathy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Pyne: It will be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if the new model for combating terrorism is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Philippines a few years ago when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he defence forces provided intelligence (and) surveillance support for the Philippines military in addressing the ISIS conflicts that occurred in the Philippines, and you would be familiar with that. ASEAN nations gave their support to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which was a much more clinical and specific engagement, as opposed to what happened in Afghanistan which was something like 25 different nations joining the coalition and whether we learned our lesson from that particular conflict. And of course, your point you made previously is a good one –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me to the Afghanistan conflict at the end.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e drawing down on forces almost 10 years ago. Of cours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that they were leaving and allowed 5,000 Afghan, Taliban fighters to be free. So, nobody comes to this, what appears to have been something of a fiasco, with entirely clean hands.
Minister: It is a messy situation. You mentioned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Marawi. There are no neat surgical operations. When there is a terrorist attack, it is not just a military operation. You also have to deal with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The solution, ultimately, lies locally. That is where the battlefront really is. It shows the limit of external intervention. To assume that we can do this remotely without leadership and resolve on the ground, locally – that is just a bridge too far. At least within Southeast Asia, I think all the governments are focused on this. We have got good counterintelligence operation information sharing. Australia has also been a critical part of this. You would know from your previous life. Like I said, we a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and to get on with it, and to know that this i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Pyne: Definitel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 think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managing of the Indo-Pacific (and) China, and its superpower status. How do you se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n its early days, certainly being just over half a year? Here in Australia, we see it very much as a return to a more consistent and probably predictable response to issues. How has Singapore and the ASEAN nations in general, seen the Biden approach to the Indo-Pacific and particularly, he has made the Quad quite preeminent in his and his Secretary of State’s views abou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How do you see that all playing out in the next three years?
Minister: Well, I share your view that at least in terms of style, in terms of the personalities involved, this is a return to a more conventional establishment, a more conventional way of operat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and the others, including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are not strangers to Australia and Asia. So that is familiar. You are on familiar ground. But I would say that the real question for us in Southeast Asia is that trade and investment is strategy. The fact that the US, having been a key locomotive for the CPTPP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t the end of the day had to walk away from it – and mind you this is not because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it is not just President Trump, but even candidate Hillary Clinton,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in her campaign also had to back away from the 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ow, I know this is because of domestic pressures, the polarisation and the division in the American body politic. Frankly, America cannot come to the table until it resolves its internal situation, achieves unity of purpose, (and) achieves confidence to engage in this. But herein lies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 because if you look at the past seven decades, the spectacular growth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equally spectacular, uninterrupted growth of Australia, a key reason for that has been the US presence here, (and) its investments in our economy – and I already told you, America is more invested here (Southeast Asia) than it is in India, China, and (Republic of) Korea combined. I am sorry I do not have the figure for Australia, but I am sure it is a very big number. And not just money – access to technology, access to markets, becoming part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is belief that free trade, properly negotiated free trade agreements, norms, rules and regulations, create a fertile environment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So I think we are all missing a key architect of that architecture and we have left the door open, certainly in terms of the CPTPP, for America to come back. I think both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certainly hope America comes back. But in the meantime, while America is out, what has happened? The RCEP was signed last year. In fact, China and Singapore were the first two countries to ratify the RCEP. Now, China has also told us that they are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and becoming part of the CPTPP. Of course, so has the UK (United Kingdom). And again, coming from a city-state that believes in free trade because, after all, trade is more than three times (Singapore’s) GDP, we have to welcome such overtures. The point is that all these big things are happening, and America does need to work out its strategy,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game in Southeast Asia is trade and investments. So that is what we are waiting for. I would not lose hope. I will continue to make that point, and to also remind America that the door remains open, and that you (America) have a head start. Do not miss out. Because after all, the real growth is in the Pacific, and America is a Pacific power. That is my elevator pitch to them.
Pyne: I think it is a good point you make. It is a good point you make, and the truth is Australia, Japan, and Singapore – wh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thdrew from the TPP – we made it clear that we believe strongly in it, and that we would keep going with it, which I think was very important. Well Vivian, we could talk all evening and we have got lots more questions I could ask you, but we have run out of time. So, can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on Global Focus. It is great to see you again an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person. And I send also Julie Bishop’s best wishes, who I was speaking with today.
Minister: Please tell her I miss her too. Great seeing you, thank you.
李光耀谈阿富汗问题讲了什么?
文 / 联合早报网
8/20/2021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没多久,扶植的政权迅速崩塌,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恐怖主义活动起家的塔利班重新上台,山姆大叔投入了20年的资源和心血一夜间付诸东流……
这几天,一些网站上载了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2009年10月接受美国著名电视记者、谈话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专访时谈及阿富汗问题的视频片段,有的中国网站的标题更称其为“神预言”。
首先要交代一下背景。美国是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进军阿富汗,两个月间就推翻了被指为九一一事件主谋基地组织提供庇护的塔利班政权。2002至2008年,美国一方面继续与塔利班在军事上缠斗,另一方面则致力重建阿富汗国家核心机构。到了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增加在阿富汗的驻军,以实施一项保护民众免受塔利班袭击并支持叛乱分子重新融入社会的战略,同时也定下从2011年起逐步将安全责任移交给阿富汗军警并撤军的计划。但上述战略和计划都不甚成功,美国与北约的作战任务直至2014年12月才算正式结束。
李光耀2009年接受查理·罗斯专访时,正是美军加大投入阿富汗战争之际。
至于是怎么“神”呢,就来看看整理自视频的问答录:
查理·罗斯:当您审视美国与其对外关系,还有它对石油和中东政治的关注时,您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分心?你认为……
李光耀:不,我不是说中东会让人分心。我认为试图在阿富汗打造出一个国家来是一种分心。在过去三四十年来,那里根本没有国家可言,末代国王被赶出去后就内战不止。

查理·罗斯:对。
李光耀:你们到底要怎么把这些小碎片拼在一起?这是不可能的。
查理·罗斯:所以,要怎么做?
李光耀:我不是专家,但我觉得你们在阿富汗获胜不是因为跟塔利班作战,而是因为你们让北方联盟与塔利班作战,并为北方联盟提供了情报和轰炸、瞄准塔利班的能力,以致他们成功取下南方。
查理·罗斯:是的,但他们在那里也面对治理问题。
李光耀:没错,但那是他们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你们的问题?
查理·罗斯:那怎么办?你会撤出所有的军队,任由阿富汗发生的事情发生吗?反正他们对美国没有那么大的威胁,是这个论点吗?
李光耀:我不知道,因为我认为再怎么难,也难不过美国让他们的军队被困在那里了。苏联军队冷酷无情,他们中有12万人在那里,但也不得不离开。
查理·罗斯:我们帮了一点忙,因为我们支持了圣战者组织。他们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支持,因为后者希望看到苏联挨打。
李光耀:但不管苏联人是否帮助他们把美国人赶出去,我认为……北约成员国对结果非常怀疑。
查理·罗斯:甚至到了不想将军队派往某些战区的地步。
李光耀:没错。是的,当然,因为那样你就会白白被枪杀。
查理·罗斯:但那些争论阿富汗是否被离弃的人首先会说,你看,苏联撤军后你曾经离弃过一次阿富汗,现在你又要离开了。美国必须坚持某些事情,并且必须对外展示它已准备好留下来。你完全不认同吗?
李光耀:不。
查理·罗斯:那你一定和你的朋友基辛格聊得很开心吧?
李光耀:不,不。
Aug 18, 2021
查理·罗斯: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你和基辛格的看法有何不同?
李光耀:我不觉得我们有任何区别。
查理·罗斯:是吗?那你怎么定义呢?
李光耀:我认为美国可以成为世界秩序的良性稳定器,没有美国,东亚当初就不会增长,你们带来了和平与技术、贸易和投资,东亚因此繁荣昌盛。
查理·罗斯:很明显,东亚发生了这种情况,你说的是新加坡和韩国。我们如何在中东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发生这样的冲突时,你要怎么做到这点?
李光耀:(笑)你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
据新加坡时政网站慈母舰(Mothership)报道,除了上述专访,李光耀2008年2月2日接受合众国际社采访时,也曾谈及阿富汗问题,他在这次访问中的谈话比较坦率,并提出部分解决方案。
李光耀说,如果美国给困在阿富汗,不应尝试做太多事情,而是让军阀之间去解决,条件是他们不会去建立一个新的塔利班国家。
他认为,要改造一个社会,是超出了任何国家的能力,以美国当年攻打伊拉克为例,应该快进快出,进去了只要委任继任者就完事了,并警告说“如果你表现得像(倒台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我就会回来”,那就够了。
美前高官傅立民:美正与中国打着注定会输的比赛
5/10/2021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自欺欺人”(self-defeating),指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对华比赛。
傅立民周日发表在澳洲亚太事务研究网站东亚论坛( East Asia Forum)上发发表题为《华盛顿正在打一场注定会输的对华比赛(Washington is playing a losing game with China)的文章,指美国应在全球性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如果继续选择与中国对抗,只会在国际社会上失道寡助。
他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凸显了弗里曼的战略动力学第三定律(Freeman’s third law of strategic dynamics),即每一次敌对行为都会引来更加敌对的反应。
文章指华盛顿发起贸易战,只是因为对中国超越美国的潜力感到担忧,并试图通过不断升级的“极限施压”来削弱、遏制中国。
他说,在国际象棋中,美国就是一个很容易被识别的选手:除了激进的开局外,没有其他的战略。
傅立民在文中以数据证明,美国老百姓深受政府发起贸易战的伤害。他指出,美国农民失去了价值240亿美元(318亿新元)的大部分中国市场;美国公司利润降低,转而削减员工工资和工作岗位、推迟加薪,并提高美国消费品的价格;据估计,美国损失了24.5万个就业岗位,同时减少了约32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要多花1277美元购买消费品;预计到2025年,美国将失去32万个工作岗位,GDP将比预期的低1.6万亿美元。
文章指出,在另一边,中国正稳步前进。2020年,中国总体贸易顺差达到5350亿美元,再创新高;与此同时,中国正通过降低贸易壁垒、与美国以外的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发起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法,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此外,傅立民还称,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主要是经济和技术上的,并不是军事上的。但现实是,“美国的飞机和战舰总在中国边界周围活动,中国的飞机和战舰并没有在美国的海岸外巡逻;中国周围到处是美军基地,而美国附近却没有中国的基地”。
傅立民强调:“如果美国继续选择对抗,只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如果美国对华政策被定义为一种道德努力,大多数其他国家将选择远离,而不是被吸引”。他指出,各国想要的是获得多边支持来应对挑战,而不是美国的单边对抗;希望在主权最大化的条件下容纳中国,而不是让中国成为敌人。
傅立民认为,除对抗无益外,中美两国合作还有许多必然性。首先,在美国国内,没有中国的参与,市场投资、供应链等很多问题都无法解决;其次,在国际上,两国应合作改革全球治理,解决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恶化、流行病、核武器扩散、全球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全球贫困等等,并为新技术制定标准。
在文章最后,傅立民强调,“为了在与中国(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国必须提升竞争力,建设一个治理更好、教育更好、更平等、更开放、更创新、更健康和更自由的社会”。他断言,显然对抗不是通往这一美好愿景的方式,合作才是。
傅立民目前是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访问学者,曾作为美国前总统尼克逊的首席中文翻译陪同访华,之后他先后在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和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陆克文斥莫里森草率介入台海议题幼稚
5/10/2021

在中澳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撰文批评,莫里森政府最近声称若台海爆发战争,澳洲将支援美国等盟友的有关言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politically juvenile),可能损害澳洲核心国家安全利益。
莫里森上周接受澳洲3AW电台的访问时说,澳洲政府对台政策将坚定不变,若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澳洲将会履行支援美国及盟友的承诺。
对此,陆克文前天(8日)在《悉尼先驱晨报》发表署名文章称,莫里森政府最近对澳洲军事介入未来美中对台湾战争的可能性所发表的草率评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可能损害澳洲核心国家安全利益。
文章说,50年来,澳洲历届政府都没有在台海冲突的课题上,公开猜测澳洲会怎么做,但在过去两周,总理莫里森、国防部长达顿,以及内政部秘书长佩祖洛,都严重违反了这一澳洲两党共识。
陆克文在文章中指出,澳洲政府此前有充分理由对潜在的台湾军事方案保持沉默(tight-lipped),因为该冲突将涉及中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力量,并有可能成为自1945年以来亚洲最暴力和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因此,澳洲现阶段不应该损害国家决策的独立性和灵活性。
文章也说,澳洲官员一直周旋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之间,竭尽全力防止此类战争发生。面对美国,澳洲官员要同美国一道,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威慑力,以此对中国大陆产生遏制效果;面对中国大陆,澳洲官员则进行游说,试图让北京相信美国会武装介入台海冲突;而面对台湾,澳洲官员要试图阻止台湾单方面宣布“台独”(或采取走向“台独”的步骤),因为这将越过北京最基本的红线。
文章接着称,莫里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像不成熟地捶胸示强(adolescent chest-thumping),不仅让美国人感到困惑,让大陆民众感到愤怒,让台湾百姓不解,也让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感到迷惑。
陆克文随后在文章中质问,为什么莫里森、达顿等要在台湾问题上,公开发出“红色警报”信号?难以想象(inconceivable)澳洲的国家安全机构会建议他们这样做,因为这不符合国家利益。“事实上,这在战略上将适得其反。”
陆克文在文中指出,目前澳洲疫苗和检疫程序一团糟、债务和赤字居高不下、执政党自由党内歧视女性问题严重,莫里森政府此时发表草率涉台言论唯一可能的动机是想转移国内视线,以获得多数支持赢得选举。对自由党来说,把工党打成“亲共”是最好的伪装。
文章称,坎培拉还有一个最广为人知的秘密:达顿和莫里森之间存在未公开的领导权之争。达顿认为,在自由党内部,中国议题是击败莫里森的最佳工具。这是可耻的,纯粹为了政治私利,用澳洲核心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做赌注。
陆克文最后在文中说,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失败,让莫里森政府难以处理澳中关系。面对复杂的挑战,澳洲领导者需要有明智、冷静和慎重的判断,国家安全不是政治游戏。然而,莫里森和达顿过去两周的表现无疑表明,面对复杂的国家安全性势,这届澳洲政府缺乏应对挑战的勇气。
China beating US by being more like America
Cultivating human capital will be essential if the US rather than China is to be the base of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By BRANDON J WEICHERT
4/25/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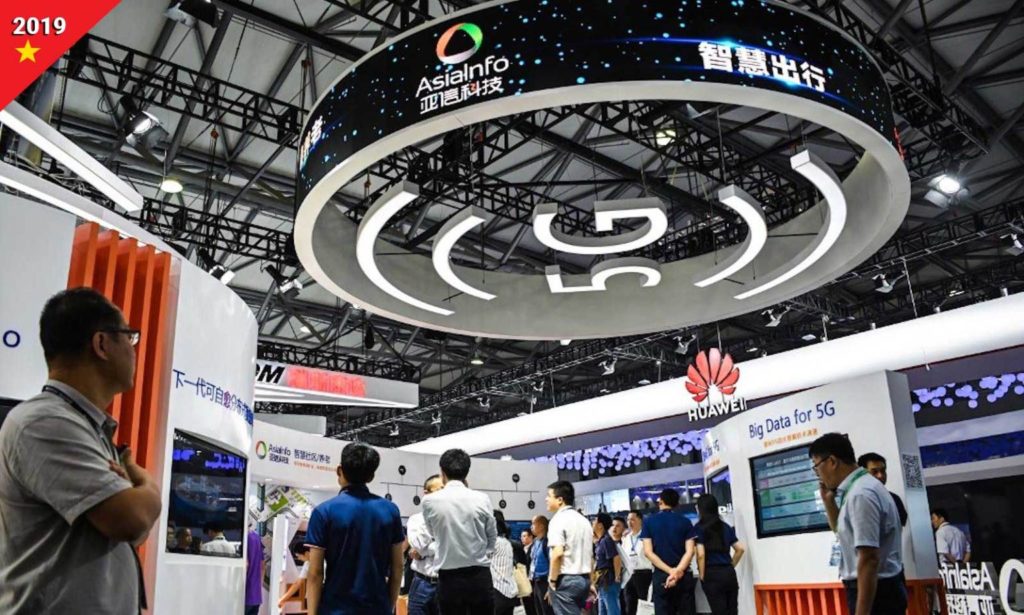
The United States transitioned from an agrarian backwater into an industrialized superstate in a rapid timeframe. One of the most decisive men in America’s industrialization was Samuel Slater.
As a young man, Slater worked in Britain’s advanced textile mills. He chafed under Britain’s rigid class system, believing he was being held back. So he moved to Rhode Island.
Once in America, Slater built the country’s first factory based entirely on that which he had learned from working in England’s textile mills – violating a British law that forbade its citizens from proliferating advanced British textile production to other countries.
Samuel Slater is still reve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Father of the American Factory System.” In Britain, if he is remembered at all, he is known by the epithet of “Slater the Traitor.”
After all, Samuel Slater engaged in what might today be referred to as “industrial espionage.” Without Slater,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likely not have risen to become the industrial challenger to British imperial might that it did in the 19th century. Even if America had evolved to challenge British power without Slater’s help, it is likely the process would have taken longer than it actually did.
Many British leaders at the time likely dismissed Slater’s actions as little more than a nuisance. The Americans had not achieved anything unique. They were merely imitating their far more innovative cousins in Britain.
As the works of Oded Shenkar have proved, however, if given enough time, annoying imitators can become dynamic innovators. The British learned this lesson the hard way. America today appears intent on learning a similar hard truth … this time from China.
By the mid-20th century, the latent industr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been unleashed as the European empires, and eventually the British-led world order, collapsed under their own weight. America had built out its own industrial base and was waiting in the geopolitical wings to replace British power – which, of course, it did.
Few today think of Britain as anything more than a middle power in the US-dominated world order. This came about only because of the careful industrial and manipulative trade practices of American statesmen throughout the 19th and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employed against British pow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ke the United States of yesteryear with the British Empire, enjoys a strong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dominant power of the day. China has also free-ridden on the security guarantees of the dominant power,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s are exhausting themselves while China grows stronger. Like the US in the previous century, inevitably, China will displace the dominant power through simple attrition in the non-military realm.
Many Americans reading this might be shocked to learn that China is not just the land of sweatshops and cheap knockoffs – any more than the United States of previous centuries was only the home of chattel slavery and King Cotton. China, like America, is a dynamic n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hile the Chinese do imitate their innovative American competitors, China does this not because the country is incapable of innovating on its own. It’s just easier to imitate effective ideas produced by America, lowering Chin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sts. Plus, China’s industrial capacity allows the country to produce more goods than America – just as America had done to Britain
Once China quickly acquires advanced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and capital from the West, Chinese firms then spin off those imitations and begin innovating. This is why China is challenging the West in quantum computing technology, biotech, space technologies, nanotechnology, 5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n assortment of other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 constitute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y reinvent the wheel when you can focus on making cheaper cars and better roads?
Since China opened itself up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70s, American versions of Samuel Slater have flocked to China, taking with them the innovations, industries, and job offerings that would have gone to Americans had Washington never embraced Beijing.
America must simply make itself more attractive than China is to talent and capital. It must create a regulatory and tax system that is more competitive than China’s. Then Washington must seriously invest in federal R&D programs as well as dynamic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those programs.
As one chief executive of a Fortune 500 company told me in 2018, “If we don’t do business in China, our competitors will.”
Meanwhile, Americans must look at effective education as a national-security imperative. If we are living in a global,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n it stands to reason Americans will need greater knowledge to thrive. Therefore, cultivating human capital will be essential if America rather than China is to be the base of the next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sides, smart bombs are useless without smart people.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understood in centuries past. America bested the British Empire and replaced it as the world hegemon using these strategies. When the Soviet Union challenged America’s dominance, the US replicated the successful strategies it had used against Britain’s empire.
Self-reliance and individual innovativeness coupled with public- and private-sector cooperation catapulted the Americans ahead of their rivals. It’s why Samuel Slater fled to the nascent United States rather than staying in England.
America is losing the great competi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because it has suffered historical amnesia. Its leaders,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like, as well as its corporate tycoons and its people must recover the lost memory – before China cements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hegemon.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all is that America has all of the tools it needs to succeed. All it needs to do is be more like it used to be in the past. To do that, competent and inspiring leadership is required. And that may prove to be the most destructive thing for America in the competition to win the 21st century.
Source: https://asiatimes.com/2021/04/china-beating-us-by-being-more-like-america/
Feb 18, 2021
Aug 4,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