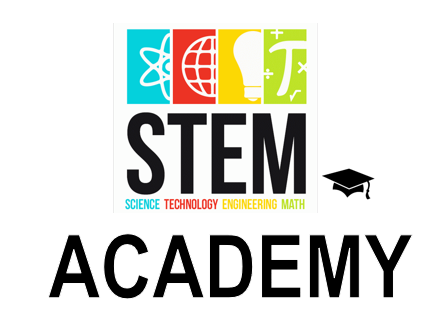美国真能对俄和解?聊聊拜登的“崇祯式困境”
By 海边的西塞罗
6/20/2021
各位好,外出刚回,看到有朋友问我对此次“拜普会”的事情怎么看,美俄真的会达成部分和解吗?跟大家简单聊两句的看法。
1
先说段历史,说明末的时候,大明江山处在内忧外患当中,内有李自成、张献忠扯旗子造反,外有皇太极公然另立朝廷。这个时候,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力亏的明廷必须先顾一头。而“攘外必先安内”,内部的李自成、张献忠其实是不可和谈的,于是与皇太极的大清议和成了唯一的选择。
但邪门的是,明明这么明确的战略选择题,崇祯皇帝就是做不出决定。其实崇祯不是没有动过议和的念头,最接近和议达成的一次,是在崇祯十五年,松锦大战惨败之后,内外交困的崇祯实在崩不住了,下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朝秘议和款。

据说和约的最终文本本来都已经拟好了,但就在这临门一脚之际,陈新甲的家童误把这机密的和款当成邸报拿出去张贴。结果弄得议和之事尽人皆知,朝堂上非议满满,实在受不住的崇祯皇帝不得不砍了陈新甲以谢清议,议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对这段很著名的史料,初看的时候大多数人往往觉得:明末清流、东林党怎么这么迂腐、不知变通——国运已然如此危及,再空谈“汉虏不两立”的高调有何用?而崇祯皇帝这人怎么这么“溜肩膀”啊?明明你下的议和令,事泄你就大大方方承认就是了,反正丑媳妇早晚也得见公婆,何必因此杀了替你办事的陈尚书呢?
可是若你再深入了解一点历史,你会发现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明末君臣这些看似迂腐愚蠢、要面子不要命的举动,背后都是理性人出于一己之私的理性博弈。
首先说,一个帝国到了末期,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是它的“战略锁定”。帝国行使它的霸权总难免遇到对手,而在与对手博弈的过程中,总难免形成“套路”。“套路”一旦形成,就会有既得利益集团依附与其上赖以谋生。这个时候帝国再想进行战略转向,就会触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晚期帝国想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是极难极难的,非大有为之君而不可为。
而这,就是崇祯皇帝遭遇的困局所在。
明末后金(清)的边患问题,是万历年间出现的,明初朝廷用来备边的饷银本来是极轻的,九边武备的军饷年例加在一起也不过数十万两而已。但努尔哈赤一扯杆子造反,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明朝军事开支成几何倍数增加,到了万历朝末年,仅辽饷开支就突破了每年四百万两。
庞大的开支不仅压垮了明朝财政,更要命的形成了一种“取天下而奉一处”的畸形体系。它如一口毒瘾,让这个帝国欲罢不能。
从“辽饷”中得利的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借此名正言顺的开始对大明其他地方的子民开始了吸血。
负责与后金对线的关宁军每年花费着大量饷银,形成了一个奢靡、稳固的军事既得利益集团。

这派人的代表,就是后来投降清朝的“平西王”吴三桂。
而整个明朝北方的物资供应体系也随之而动,商贾、物流都跟着饷银往关外走,这些依靠辽饷制度供养的商贾集团,成为附庸在关宁军事集团至上的第二层“辽饷制度得利者”。

这些人也就是晋商的前身。
而关宁军阀和商贾们又内结朝堂言官,将“平辽”的重要性在“汉虏不两立”的重要性,上升到不可动摇的“政治正确”高度……

这派的代表人物,比如东林领袖钱谦益。
有意思的是,这三派指着“反清”吃饭的人,后来在清军入关后都跪的最快,从“誓不降清”到“水太凉”切换的那叫一个丝滑无缝。足见什么“平辽”“反清”对他们不是信仰,而是生意。
而在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加持下,明朝的“战略之舵”已经锈死了,任何想让明朝从辽东这个战略方向抽身的动议,都要面对辽饷供应的关宁军阀、依靠辽饷发财的输粮商贾和被他们所收买朝堂“清流”这个庞大的“政商军抱合体”。
即便强大如皇权,想挑战这样的巨无霸,也难免心虚。
依靠东林党支持上位的崇祯皇帝,本就非什么雄才大略之主(虽然他自己以为自己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他能想到也只有“来骗、来偷袭”——想先秘密议和,把生米煮成熟饭,再逼既得利益集团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于是把议和弄得跟做贼似的。
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事儿最后还是机缘巧合下走漏了风声。事崇祯只能很“不讲武德”的给他办事儿的陈新甲杀了,因为除此之外,他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向力量大的吓人的“政商军抱合体”谢罪。
晚明的辽东“战略锈死”,就是一个手段绑架目的、工作团队绑架股东的可悲而可笑的故事。

2
明了了“明朝那些事儿”,我们再看美国总统拜登最近对俄的一系列怪异言行,你就明白他到底在纠结什么了。
当地时间6月16日,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两小时的面对面会晤,随后美俄代表团也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讨论。这是拜登上台以来美俄首脑之间的首次会晤,双方到底谈成了什么备受外界瞩目。

其实通过综合分析,拜登指望此次会谈达成的目的不言而喻。在见普京之前,拜登刚刚结束了G7首脑峰会,联合英、法、德、日、加、意这六个盟友发表了一纸对华极不友好的共同声明,拉着盟友组团与中国抗衡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这节骨眼上会见普京,即便拜登没有乐观到指望离间中俄,至少也是希望能和这个老对手“暂时休战”,这样至少可以减少美国的一个战略方向。
但老拜的这个愿望能不能达成呢?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会谈结束后,拜登与普京甚至没有召开了一个联合新闻发布会。而是各自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而在拜登那一场记者会上,出人意料的遭遇了曾支持他的众媒体的“围攻”:
“总统先生,你有没有就乌克兰问题向普京总统提出抗议?”
“你有没有就同性恋议题向普京表达美国态度”
“你有没有就俄反对党的处境问题表示关切?”
“你在竞选期间曾称普京为‘杀手’,如今你依然支持你当年的观点吗?”
这些如此不给本国总统面子的追诘,问的可怜的老拜语无伦次,无数次冒出类似的语句“额……实际上,我——呃,听着,他已经说清楚了,呃……答案是,我相信,他过去基本上已经说,他会做,他要的……呃…或者确实,做过某些事情…”

看的我都替老拜着急。
最语无伦次的时刻,拜登还口误将普京说成了川普。
我觉得拜登确实应该在此时想起川普,因为他如今遭遇的围攻,颇似其前任川普在位时“舌战群儒”的情景。而这位当初竞选时获得几乎所有美国左派媒体支持总统,如今似乎没有得到任何一家曾经支持他的左媒的怜悯。
即便他狼狈而仓促的宣布记者会结束后,曾经亲善他的CNN依然穷追不舍:“总统先生,你凭什么认为普京能做到他对你许诺的那些?”
老拜此时估计是终于绷不住了,回头大骂记者:“你干错行了吧?”——口气与川普当年说“Fake News”迷之神似。

我觉得,美国主流媒体与拜登在此次记者会上的翻脸是令人惊讶、而又在意料之中的。这证明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就像明末的东林党对崇祯皇帝的支持其实是有条件的一样,拜登作为美国“反川普大联盟”的领袖,美国主流媒体对其的支持同样有着不明说、但非常严苛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与俄罗斯和解关系。
无论对拜登还是对川普,美国主流媒体和其背后所代表的势力,为什么不允许总统“与俄媾和”?
因为与晚明相似,美国目前所遭遇的,也是一种深度“战略锈死”。
3
众所周知,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围堵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是一段足够长的时间,长到了美国在军事、经济、舆论和政治领域都已经形成了强大既得利益集团,养成了依附于这种国家战略谋取他们利益的惯性。
在军事上,整个冷战时代,为了防备假想中的“赤色狂潮”席卷欧洲,美国一直在西欧维持了庞大的军事存在,苏联解体后、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都曾试图通过削减欧洲驻军来甩掉这个沉重的包袱,但这种裁军在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总是莫名其妙的难以为继。事实上,围堵苏联的北约在冷战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继续东扩,美国在欧洲承担的军事防备任务没有消减,反而更重了。

而在工业、经济领域,夸大苏联\俄罗斯的对美战略威胁,以便争取更多联邦拨款的所谓“军工复合体”早在冷战末期就是让里根总统也不敢惹的存在。而由于苏联\俄罗斯石油主产国的地位,在美国颇有发言权的能源工业巨头们也对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缺乏兴趣。
冷战结束之后,对俄罗斯的继续围堵还越来越受到外交层面的掣肘,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由于被美国“包养”惯了,对类似川普所主张的“欧洲应当保卫自己”的提议十分反感,实际上并不愿意看到美俄和解;而沙特等中东盟友,出于石油经济的考虑,也希望美国与俄继续对抗。
当然,最为强大的还是美国国内舆论的压力,拜美国自冷战初期就开始的反苏宣传所赐,美国主流媒体对苏联和俄罗斯成见极深,这种在上述各类游说集团的“资助”刺激下,成为美国媒体一门既能拿钱,又“政治正确”的便宜生意。在美国,指责总统对俄态度过于友好是绝对的政治正确。不管这个总统是是川普,还是拜登。
事实上,上一任总统川普可能是冷战结束以后唯一在竞选期间没有大骂俄罗斯,却能成功上位的候选人。而殊堪玩味的是,他在上台之后立刻遭遇了严厉的“通俄门”指控,而操刀进行这次指控,不乏眼下在给拜登打下手的那支民主党团队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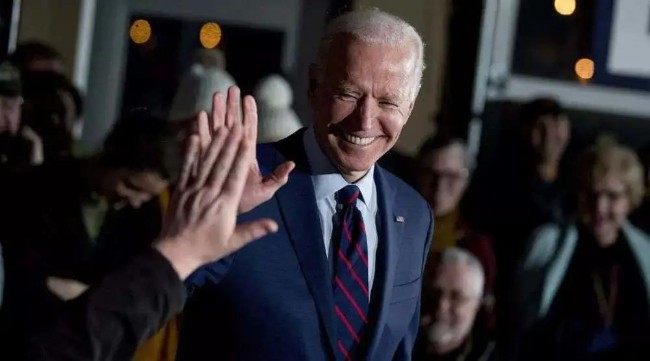
所以,如同明末的“平辽”表面是政治正确,实则是门生意一样。“反俄”在美国也是一门牵扯既得利益集团过于巨大的“生意”。政坛老滑头拜登同志当然是深谙此道的,他在上台前屡次表态“俄罗斯仍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其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和取悦被川普“通俄”得罪的军工政商媒抱合体。
但讽刺的是,在依靠此招登上总统宝座之后,拜登不得不去做他当年所誓言反对的事情——正如与清的媾和是晚明唯一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与俄罗斯的和解是美国当下必须做的事情。虽然这样的调整对同样“战略锈死”的美国来说,真的很难做出。
那么拜登能完成这次艰难的转向吗?我觉得基本没戏。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在瑞士刚刚发飙骂完记者“干错行”之后,回到华盛顿的拜登当天刚下飞机,就立刻道歉,称自己“不该失去理智”云云……

总统对一家媒体这么“秒怂”,不仅对忍了“头铁”的川普四年的美媒来说肯定是个惊喜,在美国历史上恐怕也少见。
但对于美国来说,这也许是可悲的。
正如扳动生锈的巨轮船舵需要一膀子蛮力,扭转已经“战略锈死”的老旧帝国的方向,也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
而拜登与当年的崇祯一样,他们太过于重视令名、爱惜羽毛。毋宁说,他们当年正是通过此招获得拥护、坐稳位置的,如今也不可能自我打脸,走向自己曾经伪装的角色的反面——虽然这种“君子豹变”,正是他们国家急需的。
也许,这就是帝国的宿命吧:一个老旧的帝国,最大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于它自身的“战略锈死”。可一个帝国越到末期,越无法推出一个能扳动这种锈死的领导人——即便出现,他也无法久居其位。

Jun 16, 2021